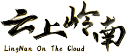
《广东通史》记载:“北路”为进出岭南的主要通道,从广州出发,沿北江而上,越过大庾岭、抵达江西,此路因时有“诸夷”贡使及公差通行,又称“使节路”。道光十八年(1838),林则徐奉旨来广东禁烟,即走此路。
丹麦人龙伯格在《清代来华传教士马若瑟研究》中也提到了,连接广州和北京的所谓的“使节之路”。在清明时期,这是一条繁忙的连接广州和北京的道路,使者、商人、传教士、考察者穿行于此道路上。
所谓“使节之路”,实际是一条连接珠江水系与长江水系的通道,或者说连接华南与华北的通道,通过京杭大运河到达北京,也是一条重要的商道。
可以说,明清时代(清朝鸦片战争战争之前),从广州进入中国到达北京的使者、商人、传教士等,都是经过了这条“使节之路”。在岭南范围内,从广州城北上,经过三水、北江,翻越梅岭,可到达江西赣江,再进入长江水系。
本文将讲述明清时代从广州进入中国的使者或旅行者,在这条“使者之路”上发生的有趣的故事,还会告诉你,当时的使者或外国人,持有什么牌照才能进入中国。
何人可进入中国?
“人们必须了解,中华帝国是对一切外国人封闭的,只有三种人法律许可入境。”这是《利玛窦中国礼记》中的一段记载,在明清时期,尤其是在鸦片战争之前的这段时间里,朝廷对外国人进入中国是严格管控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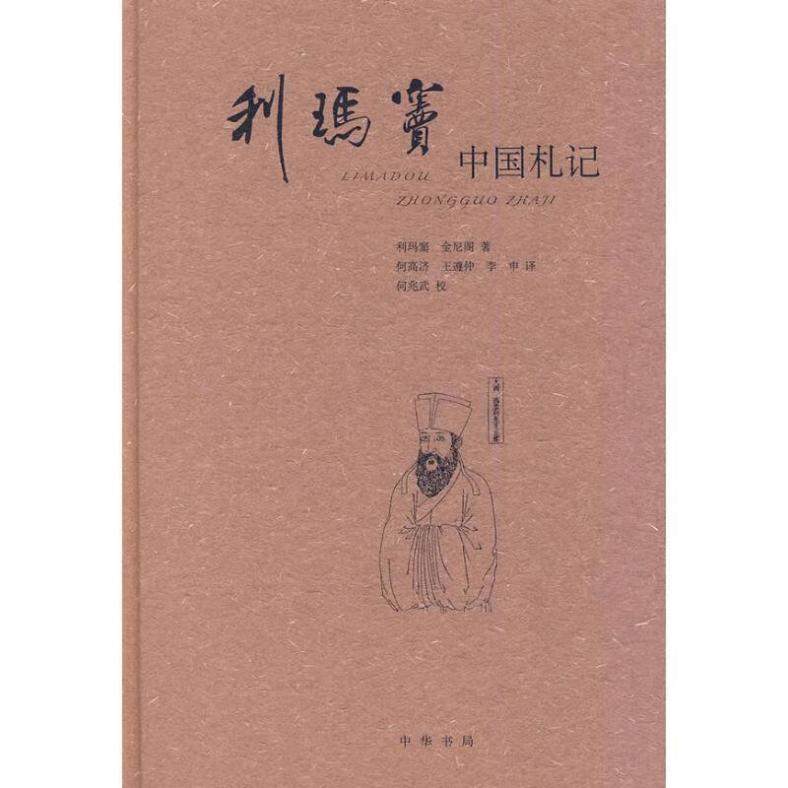
那么,对于哪三种人可以进入中国呢?利玛窦说,第一种人是从邻国每年自愿前来向中国皇帝进贡的人,即“贡使”。第二种是一些商人,虽然不希望被看作是来进贡的,但慑于中国的幅员广阔,就来向皇帝致敬,尊他为万王之中的首领和最伟大的一个。这些人都是来寻求财富的,但一般是打着被本国的君主派来的“使者”旗号,才能进入中国。再就是,非常羡慕这个伟大帝国的声名,而希望来此永久定居的人。
可以说,前两者是多数的情况。在明朝,而这些人从广州或澳门进入中国后,再通过“使者之路”进入北京。
比如,曾在北京定居的葡萄牙传教士安文思在《中国新史》一书中说,“我本人在1656年,奉皇帝之命,从北京到澳门,水路走运河及其他几条河,大约六百里格,只走了一天的陆路,以越过江西和广东分界的山岭。”他说的两省的分界山岭就是“梅岭”,通过此山岭的道路称其为“梅关古道”。

再如,英国曾两次派外交使节团来中国访问,一次是1793年的马戛尔尼使团,另一次就是1816年的阿美士德使团。前者是从北京返回的时候,自南向北经过了“使者之路”到达广州,而后者则是从广州进入中国,然后自南向北到达北京。
根据《消失的铺路人-罗明坚与中西初识》的记载,在明朝时期耶稣会士教士罗明坚,1585年曾在肇庆居住过,他乘坐的船队从三水后转入北江,留下在这条路上的记载:
“船在宽阔的江面上继续航行。一天,空中突然飘落雨点,霎时江天烟蒙一片,两岸墨染如黛,随着船缓缓前行,周围的景色如水彩画般一张张向后翻卷。罗明坚触景生情,突然诗兴大发,用汉语写起诗来....”当他到达梅岭后,又写了一首《度梅岭》汉语的诗:“乍登岭表插天高,果见梅关地位豪;今日游僧经此过;喜沾化雨湿长袍。”在他的笔下,这条“使节之路”上的北江两岸,“山岭峻拔,细雨沾襟”,充满了诗情画意。
上述英国使者确实是他们国家派出的,耶稣会士教士也是以传教为目的,但确实也有一些商人,打着使者或进贡的旗号,进入中国,比如《利玛窦中国礼记》中说,中国接纳来自其他很多国家的这类使节,如交趾支那、暹罗、琉球、高丽以及一些鞑靼首领,他们给国库增加沉重的负担。中国人知道整个事情是一场“骗局”,但他们不在乎。倒不如说,他们恭维他们皇帝的办法就是让他相信全世界都在向中国朝贡,而事实上则是中国在向其他国家“朝贡”。
客观上讲,这些往返与中西之间的使者或商人,促进了中西文化交流,但在现代人看来,明朝朝廷的做法,是不是更有些迂腐?纯从经济角度讲,完全是“赔本”的生意。
进入中国的礼遇
“明朝政府并无经济诉求,封其为属国,只是为了宣示国威、怀柔远人。几千年以来,中国认为幅员辽阔的华夏即为世界的中心,周边之国属于蛮夷,蛮夷须接受华夏教化;这种天下观念所衍生的对外国策,就是严夷夏之防和以文德怀柔远人。”这是《消失的铺路人-罗明坚与中西初识》一书的记载。
可以说,在明清时期朝廷坚持既要“严防夷人”,又要“怀柔远人”。在这情况下,基于孔子“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的思想,一旦有允许进入中国的使者,还是会得到很好的礼遇,一路上的吃住行都有朝廷或当地官府承办,我们来看看经过“使者之路”的外国人,又是怎么记录这一现象的呢?
“所有以使节身份进入中国的人,无论他们为友好国家所派还是敌对国家所派,都会受到认真接待,受到尊重并接受馈赠,对待他们就像对待皇帝亲自来访一样。”这是西班牙人胡安·冈萨雷斯·德·门多萨根据从澳门到内地的传教士提供材料,于1585年编辑出版的《中华大帝国史》中的一段话。

他还在书中十分生动地说,外国人一进了国门,无论在哪个省,该省的高级长官或总督便亲自出来迎接。迎接他们的还有城里官员、官兵护卫。使者一下船就不能让他们的“脚沾地”,即便路并不长。为此,岸上一定有一个轿子和8个抬轿的人等在那里。轿子用象牙或其他贵重的材料制成,用天鹅绒或锦缎、花缎围好。
我们可以看出,明朝时期,朝廷为了体现“怀柔远人”,不惜成本的接待这些外国人,将其当做贵宾待遇,积极做好每个环节。他们沿途的吃住又是怎么样的呢?对此《中华大帝国史》中说“为了迎接外来宾客,皇帝命令在全国各主要城府建立官舍,这些官舍非常适于这些人以及外出办差经过此地的官员留宿。官舍有官兵把守,内部装饰豪华。睡床、帷帐、服务设施等一应俱全。”
实际上,沿途的驿站,不是专门为接待外国人而建立的,但朝廷让上述“官舍”,完全免费接待这些外国人,而且还想方设法保证他们的人身安全。而对于明朝朝廷大量免费接待外国人,就一定得到他们的认可吗?未必,这些外国人,要么要实现他们“传教”的目的,要么实现扩大“贸易”的目的,而非是否享受免费的接待。
进入中国的证件
对现代人来说,外国人进入中国,或中国人出国,必须持有“护照”和进入国家的“签证”,那么,对于明代时期,外国人进入中国是否需要有类似的证件呢?
“像我一样记载中国的作者较少,况且来中国首先要克服重重困难,还要获得通关令牌和许可证书,因此,除在交易会时期进入广州城河那里和城墙外河岸边的那一小块郊区以外,几乎没什么人进入中国的其他地方。”
这是曾在潮汕地区被广东官府关押和旅行的西班牙人阿德里亚诺·德拉斯·科尔特斯,根据他在岭南旅行期间的观察和记录,于1625年出版了《中国纪行》一书中的记载,我们从中可以看出,当时的外国人进入中国,必须有“通关令牌”。那么,这种令牌是什么样的呢?
对此,《中华大帝国史》中有详细的介绍:行牒是一块白牌子,上面用大字写着该使者国籍和由何人所派。它由一个人捧着,一直走在队伍前面。由内阁签发的允许使者前往皇宫的行牒与一般行牒区别很大,其质地是着色的羊皮纸,上有皇帝的大印,由一人高举过头,走在队伍前面。只有皇帝和巡抚直接下令才能发这种行牒。
《中华大帝国史》记载神父从广州进入中国的时候说“众人前走出一人,手持白色木牌,上边写有黑色的大字,后来他们获悉那就是广州总督发给他们的行牒。有了它,他们方可登陆,否则禁止任何外国人入内。”
我们可以看出,外国使者进入中国内地,需要持有“行牒”,这些牌照至少需要地方大员签发,如“广州总督”,进入北京甚至还需要皇帝签发,而对于外国人,一旦获得了这种“行牒”,不但在国内畅通无阻,而且吃住行都由当地官员来接待和安排。
对于外国人上述记载的“行牒”,《广东通史》中记载了一种“勘合”制度,说这是明朝发给海外诸国前来朝贡的凭证,领有勘合,始准贸易。洪武十八年(1383),礼部向暹罗、占城、爪哇、真腊、满剌加、苏门答剌等国颁发第一批勘合。但“勘合”与“行牒”是不是一种证件,还需要我们进一步考证。
正因为“行牒”如此之重要,一些打算进入中国的外国人,想方设法得到它,对此,《中华大帝国史》中说:中国沿海的总督有时不顾海禁,只要有人给他送礼,他就秘密签发行牒,允许中国人出海,而对于他们而言,只要外国人想他行贿,他们也签发行牒给外国人,允许外国人进港买卖各种商品,不过他们要首先接受严格的检查和盘问,并告知发给他们的是定期行牒,他们只许做生意,不许在城里滞留,不许窥探中国的秘密。
比如,上文提到的意大利传教士罗明坚,以自鸣钟表当作贵重礼物送给了当时两广总督陈文峰,最终留在了中国。
名家简介:

董兴宝,山东潍坊人,国家一级注册建造师,现为广东省作家协会会员、山东省作家协会会员。在广东工作6年,曾担任广东清远市政府文化顾问(2014-2018年)。主编出版过《北江茶道》(南方日报出版社2014年出版)、《清远故事》(新华出版社2017年出版)和《中华洞河之道》(广州出版社2018年出版)等书籍。
-
【名家说岭南•董兴宝】盐商与盐官—外国人笔下的岭南风土人情(18)
2024-08-12 21:49:12 -
聚焦粤菜形成关键期的饮食文化,《广东食语》正式出版
2024-08-11 10:51:07 -
【名家说岭南·江冰】广州博物馆与中国大酒店联手,让“消失的名菜”重上餐桌,“食在广州”锦上添花活力四射
2024-08-09 12:24:14 -
【名家说岭南•董兴宝】海幢寺—外国人笔下的岭南风土人情(17)
2024-08-08 18:50:3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