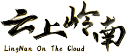
历史上,清朝政府为了增加财政收入,曾在全国各地设立“关卡”,对路过的商品收税,这就是清朝历史上的“厘金”制度。我们来看看在外国人的眼里,这个制度是如何设立的,在广东的情况又是如何呢?
厘金的起源
“在19世纪中期,在传统田赋、盐税和关税以外又增加了两种率,第一种是1854年以后成立的大清海关正式规定向对外贸易征收关税,并把收入上缴给北京政府而不归各省掌握。第二种新税——厘金税制则相反,它原来是各省官员为了筹资镇压太平军而设立的。”
这是美国历史学家、国际汉学泰斗费正清编撰的《剑桥中国晚清史》中的一段记载,从中可以看出,“厘金”是在清朝镇压太平天国过程中产生的一种税,而且由地方政府收取。

该书中还强调,这种“过境税”——厘金税于1853年首先在江苏省开征。但到了1862年,它几乎适用于一切商品,并且差不多各省都已征收。在有些情况下,不但在运输线沿线征收,而且还在出发地作为生产税或者在目的地作为营业税征收。
清朝各地方政府充分利用各自“收税”,税率还悬殊,从货价的1%到10%不等,而最普遍的税率是每个厘卡收2%。在各省每年向户部上报的商品厘金税中,中央政府只能处理约20%,其余的实际都归各省掌握。未上报的数量不详的税收当然也归地方留用。在这种情况下,地方收税的积极性显然很高,但也坑苦了百姓和商户。
对于清朝政府开征的“厘金”税,《德国汉学家福兰阁论中国》一书中也有描述:厘金是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30年代,中国国内贸易征税制度之一。最初是地方筹集饷需的方法,又名“捐厘”。厘金制度出现之初,不但可以代替当时因太平天国起义而处于瘫痪状态的国内常关的职能,而且还使厘金收费卡有随战区的变化“因地制宜”设置的灵活性,因而增加了清政府的税收。
恰恰是这种“因地制宜”的灵活收税,形成了地方乱收税的情况。那么,广东对于“厘金”收税情况又是如何的呢?
德国《法兰克福报》的记者保罗·戈德曼,到中国考察后写下了《1898年的夏日:一个德国记者的中国观察》一书,该书中写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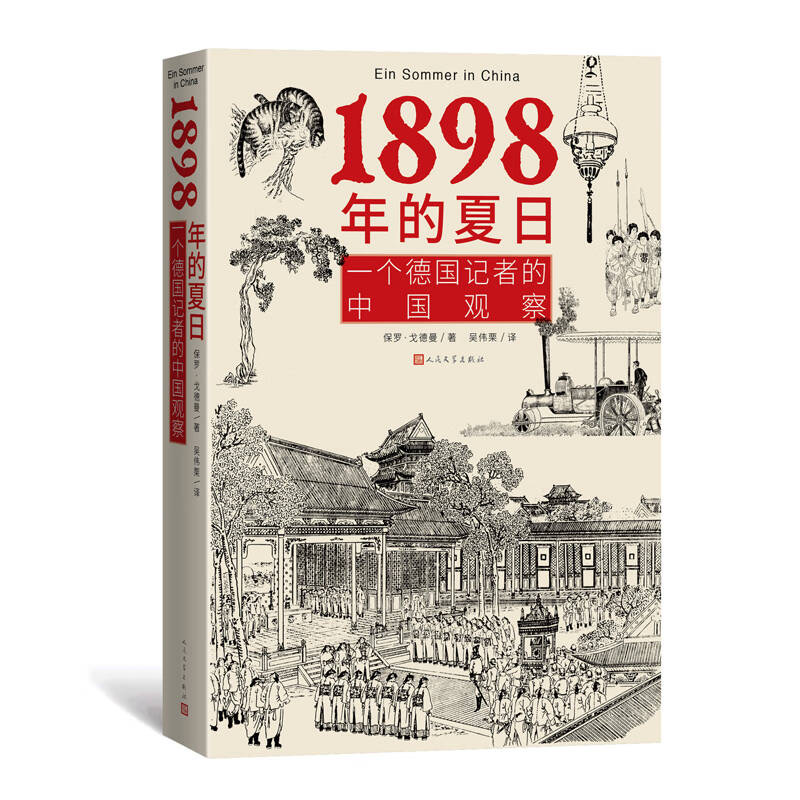
广东产生了中国第二个海关——厘金局:由地方机关收取厘金。厘金局只针对海关通过的进口货物,当货物从港口再次运往内陆时才收取。广东的厘金局就设在海关局旁边,并以地方政府之名要求纳税。
在这种情况下,平时进口货物只缴纳关税的外国商人,显然不乐意了。
当然,在广东及国内各地,清朝各地政府收取的这种厘金税,不仅仅是针对进口货物,在国内流通的货物,同样进行收税。对此,英国汉学家约·罗伯茨(J.A.G.Roberts)在《十九世纪西方人眼中的中国》中刊载了《通过华南边疆从广州到曼德勒旅行记事》的一篇文章,该文章的作者见证了收取厘金的情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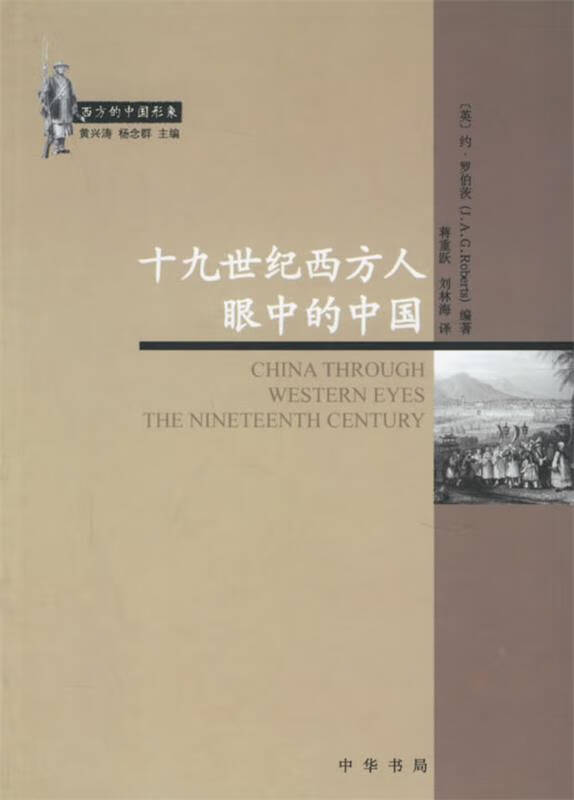
我们每天都要经过一两个收取厘金的站点,即税卡,因此,随运输路程的增加,货物的成本亦不断上涨。事实是这些关税“壁垒”使贸易处于瘫痪状态。这些税卡一般是一艘大平底船,上面搭了亭子供小官办公用,厨房在旁边的另一条船上,这些东西都建造得很奇特。
该文的作者还说,当他们靠近这些税卡时,船夫无疑很紧张,但强装镇静,急急忙忙地向检查的人报告说他们船上拉的是外国人,一旦被放行时则如释重负。为什么他们在税卡显得惴惴不安——因为,他们无疑是在走私盐。
这种设卡收税的“厘金”制度是谁最早帮助清朝政府提出来的呢?美国汉学家费正清在《中国沿海的贸易与外交-通商口岸的开埠(1842-1854年)》一书中给出了答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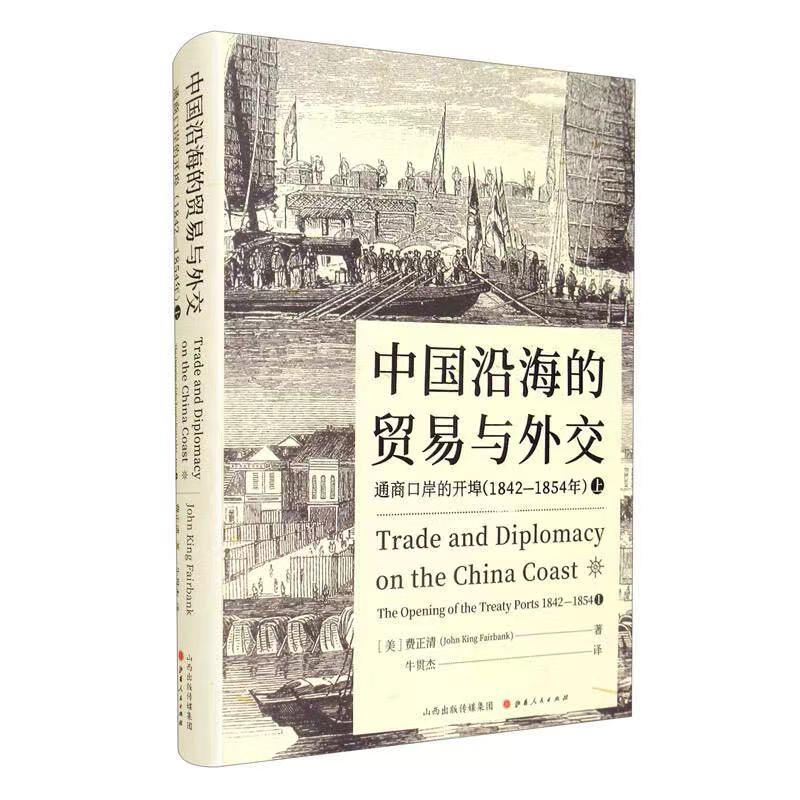
雷以诚是一位财政专家,他提出了著名的厘金制度,厘金在太平天国时期支撑了清朝的财政,然而在此后一直阻碍着中国国内贸易的发展。
反对的声音
“今幸皇上深知损纳之弊,谕令各省停捐,甚盛事也。惟是厘金各局,虽能暂救国用之支,奈司事人役,每多冗滥,暗侵公项,以肥已囊,且贻害商民,滞消货物,陆续裁撤,实不能无望于当道者。”
这是1865年来华并在广州居住的德国传教士花之安,被誉为“最有学问的汉学家”,在其著名的文言文作品《自西徂东》中的记载,在他看来,厘金制度虽然当时是为对付“天平天国”运动救急,但弊端也很多,应该裁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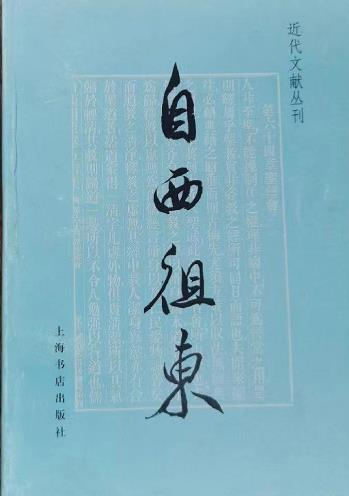
《剑桥中国晚清史》中引用广东清末民初的实业家、思想家、教育家、文学家郑观应的观点:为了促进商业,政府必须改革税制,废除地方贸易中的厘金税。
19世纪后期至20世纪初英国著名汉学家翟理思在《中国和中国人》一书中说,只要中华帝国的税收是老百姓们熟悉的种类,他们就会乐意交税,就算在困难时期也不会有什么抱怨。他特别列举了“厘金”的例子,从中可看出中国老百姓保守顺从的特点。即使在损害他们自身利益的情况下,他们仍然任劳任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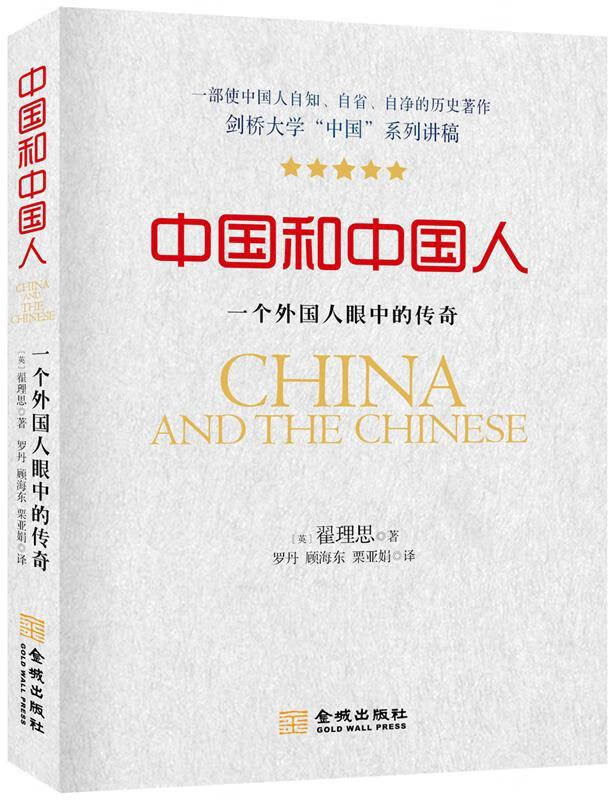
这位英国人也提到,“厘金”最初是从所有商品的销售额收取1/10,用来弥补“太平天国运动”引起的土地税不足和其它的破坏。这笔钱的用途是支援军队,因此也被叫做“军税”,而且税务衙门是把这项税收作为临时的应急费用来征收的。
但是,40年后,“厘金”却继续作为一项帝国的基本税收向老百姓征收,而反对这项税收的,还有外国商人,因为“厘金”影响到他们和中国的商贸交易的生意收入。这一观点也与《1898年的夏日:一个德国记者的中国观察》表达的观点类似。
厘金对清朝的重要性
除了上文中提到的厘金对清朝应对太平天国运动起了重要作用外,在清朝政府的财政收入及对外借款中,厘金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剑桥中国晚清史》中说,18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清朝帝国的收入与19世纪中期收入相比几乎增加了一倍,但这几乎要归因于关税和厘金税。
书中还列举了19世纪70年代末,大清帝国的总税收,包括中央和地方在内,计约6000万两。虽然最大部分的收入仍然来源于田赋,但厘金仍达到1800万两(占30%),关税达到1200万两(占20%)。可以看出,厘金收入对清朝政府的重要性。
另一方面,清朝政府正是因为有了厘金收入,才能从国外列强中继续借款,维持统治。
对此,日本著名历史学家、汉学家滨下武志在《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清末海关财政与通商口岸市场圈》中提到,在1898年2月的英国、德国向清朝政府的续借款,由汇丰银行和德华银行担当,担保就是厘金和盐税。当然,之所以叫“续借款”是因为在甲午战争后,清朝政府已经向英国、德国银行借过款。

尽管厘金对清朝政府非常重要,但西方列强一直要求取消这种税,尤其是对于一些通商口岸。例如,
《剑桥中国晚清史》中说,1876年9月,烟台条约规定开辟四个新的通商口岸,并限定通商口岸应为豁免厘金税的区域。
《德国汉学家福兰阁论中国》一书中则说,1902年9月5日,中英签订了《续议通商行船条约》,福兰阁就此发表了《厘金问题》和《厘金和中英续议通商行船条约》的报道。由于外国商人在中国也要交纳厘金,而且厘金的税额还非常高,英国强烈要求清政府取消厘金。英国人允愿进口洋货加税一倍半,也要清楚将“各厘卡及抽类似厘捐之关卡概予裁撤。”
关于外国人反对厘金的问题,美国历史学教授斯文·贝克特(Sven Beckert)在其著作《棉花帝国:一部资本主义全球史》中也有讲述:欧洲商人和欧洲政府对中国施加压力,要求其进入市场。例如,《烟台条约》规定了进一步开放沿海和沿江港口城市并废除了厘金。1877年,一位西方商人说:“外国商人已经耐心地等待着达成这些目标好久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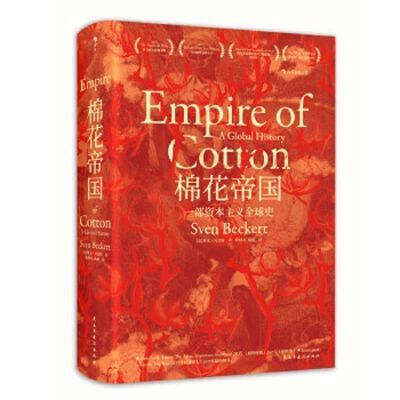
【名家简介】

董兴宝,山东潍坊人,国家一级注册建造师,现为广东省作家协会会员、山东省作家协会会员。在广东工作6年,曾担任广东清远市政府文化顾问(2014-2018年)。主编出版过《北江茶道》(南方日报出版社2014年出版)、《清远故事》(新华出版社2017年出版)和《中华洞河之道》(广州出版社2018年出版)等书籍。
-
【名家说岭南•江冰主持】南粤风度与川渝气质
2025-01-24 17:39:24 -
【名家说岭南·江冰】五仙观被誉为“羊城祖庙”,我在这里突然醒悟了根系的意义
2025-01-23 10:25:48 -
【名家说岭南·江冰】颂今广东音乐新作音乐会:我用中原、岭南、大海三只耳朵悉心聆听
2025-01-20 11:21:47 -
【名家说岭南·康毅】岁末迎大寒 康毅带您“行花街”品浓浓年味
2025-01-20 06:24:3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