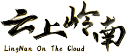
自20世纪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经过广泛西方化、专业化的影响之后,饶宗颐继承王国维、陈寅恪先生等前贤,走出一条在现代学术与国际汉学背景下回归中国学术传统的独特之路。他努力在“博古通今、中西融贯”这个层面上回归中国学术传统。他在学术史上的得失轩轾,大致缘于此。
饶先生在学术研究上,快意于开疆辟土,而不经意于屯垦戍边。他的治学特色是创造性优于严谨性。就其特定领域与具体问题的研究而言,论证未必都周全严密,结论未必皆精当不灭。但他的研究容或有粗疏,决无凡庸平浅;容或有零碎,决无框框套套。
他给学界留下宝贵遗产,也留下继续探讨的空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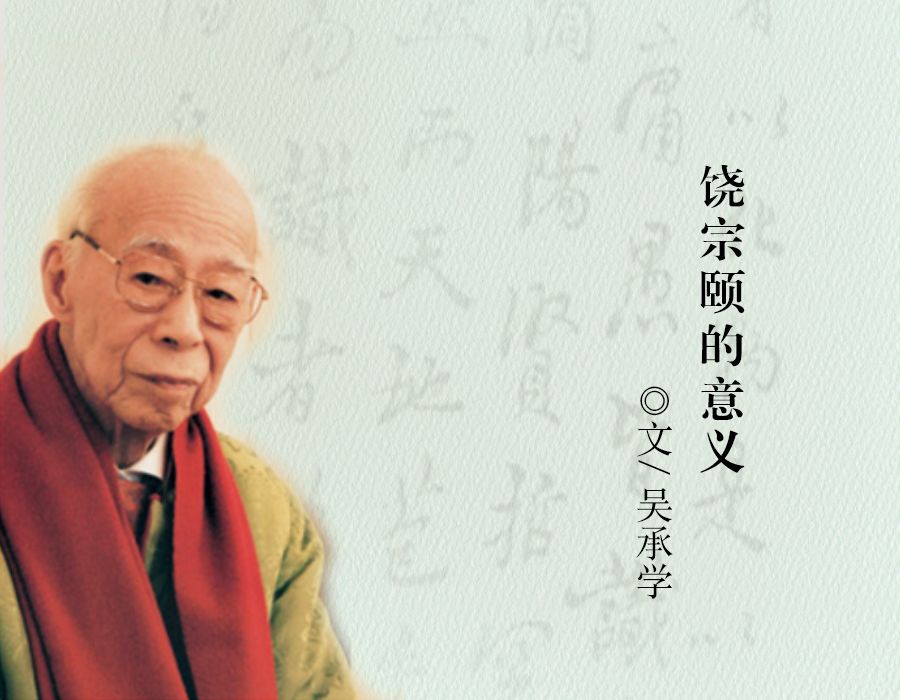
饶宗颐先生(1917—2018)已成中国学术史的一部分。按学界的说法,饶先生的学术研究包括:史溯、甲骨、简帛学、经术、礼乐、宗教学、史学、中外关系史、敦煌学、潮学、目录学、文章学、诗词学、艺术等多个领域。唐人诗云:“倾国宜通体,谁来独赏眉。”倾国倾城之貌,在于整体之美,而非局部。对饶先生这样的学术通人,应该“通体”把握,才有可能准确地评价其学术成就与地位。但是,要真正把握其学术“通体”,绝非易事。真正有能力全面、深入研究和评价饶宗颐的学者,也应该是学术“通人”。多数按分科培养的现代学者,只能在某个学术领域里讨论饶先生。虽然这样难以遍识饶先生学术“通体”之美,但“独赏眉”也不失为快意之事。故笔者不揣浅陋,管窥锥指,恭待高明指教。

饶先生治学领域非常广阔,但他明确说明其研究基础是语言文字学与文学:“中国的学问全是以文字学和文学做根柢,没有这两个东西其他都是空的。”[1]“我研治许多问题喜欢从语言上追上去,清代朴学的重要特征就在于非常重视文字音韵训诂校勘考证这一类的工夫,认为这是一切学问的基石。”[2]他特别强调研究中国文学要尊重中国语言文字的独特性,不能套用西方理论:
中国靠文字来统一,尽管方言繁多,而文字却是共同而一致的。这显示中国文化是以文字为领导。中国是以文字→文学为文化主力,和西方以语言=文字→文学情形很不一样。这说明纯用语言学方法来处理分析中国文学,恐有扞格之处;尤其是诗学,困难更多。至若轻易借用西方理论来衡量汉诗,有时不免有削足就履的毛病了。[3]
饶先生长期研治甲骨文、金文、战国秦汉文字,由文字而及文学,拓展了早期中国文学研究。
掌握包括国外古典语言在内的多种语言,是饶先生治学的重要利器。他的名作《〈文心雕龙·声律篇〉书后》一文,从梵文的语音结构入手,来研究四声、音纽、反切之来源,认为“悉昙”是印度学童学习字母拼音的法门,随梵书东传进入中国,晋时道安已传其书。汉语四声之说,是受到悉昙影响而产生的。提出与陈寅恪先生《四声三问》不同的观点,在学术界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并引发相关的讨论。《梵语Ṛ、Ṝ、Ḷ、Ḹ四流音及其对汉文学之影响》一文,从梵语对汉语语言学的影响进而论及对文学的影响。饶先生从鸠摩罗什《通韵》的研究追溯到Ṛ、Ṝ、Ḷ、Ḹ四个梵文字母译文为“鲁流卢楼”,而唐代《悉昙章》以“鲁流卢楼”为和音,遂对中国宗教以及词曲文学的和声形式产生深刻影响。他以之解释张炎《词源·讴曲旨要》“哩字引浊啰字清,住乃哩啰顿㖫㖮”,其中的和声,就是出自《悉昙章》。而唐代宴席的“合生”,唐以来唱偈、道情、民间戏曲,乃至汉文化圈一些国家的艺术文学作品中,都有类似情况。“以‘哩啰’为和声的技巧,已由鸠摩罗什传到了现代。悉昙无意中影响中国文学达八世纪左右,甚至道教等宗教信徒笔下,都有其遗声可寻。”[4]这些研究考察外来语言对中国文学之影响,眼光独特,给人启发良多。
饶先生善于从语言学角度拓展传统学术领域的研究路径,他的《“言路”与“戏路”》一文讨论语言与古代戏曲发展、传播之间的关系,从戏文与方言的互相印证中,考证古代戏剧不为人知的传播路径。如1975年潮州出土明宣德六年《刘希必金钗记》写本,他用语言学的眼光加以审视,敏锐指出:“南戏的‘戏路’传播途径,是从温州经福建至潮州,然后到南洋群岛和越南各地。”[5]南戏的“戏路”正是随着以闽南方言为核心的“言路”广为流播。
饶先生的研究体系宏大,但他始终把文学视为所有学术研究的重要基础。他在上世纪80年代就明确说过:“一切之学必以文学植基,否则难以致弘深而通要眇。”[6]晚年时他又说:“一切学术,均需以文学作底子。文学好,就不怕其他不好。”[7]这种说法,决非应景而发,而是饶先生独到的治学体认。按照桐城派理论,文章之义法,不外“言有物”与“言有序”,而这两者的确是一切学术的基础。然而,饶先生不但以文学作为其它学科的根基,而且认为必须以文学为根基,学术研究才能“致弘深而通要眇”,这是对文学作用的高度认同。他说的文学,当然不仅指学术研究,也包括文学创作在内。古往今来,绝少人如此强调文学之重要性。饶先生没有进一步阐释为什么“一切之学必以文学植基,否则难以致弘深而通要眇”,以意推之,是因为真正文学之妙,在于能敏锐地感受世间万事万物最微妙之处,能写出人类最为复杂细腻的思想感情。文学构思必须具有“观古今于须臾,抚四海于一瞬”这种超越时空的想象力与创造力,也包括语言文字的运用,与思维逻辑是相通的。正因为文学必须具有感受力、想象力、创造力、语言表达能力以及思维逻辑,所以饶先生把文学看成是一切学问的基础,有了这个基础,就可以做好其它学问,并达到“致弘深而通要眇”境界。
饶先生在中国文学研究方面,几乎涉及上古至近代中国文学各个时代与各种文体,涉及文学史与文学批评,主要可以归为几大领域:楚辞学、赋学、文选学、敦煌文学、文章学、诗词学等。《饶宗颐二十世纪学术文集》共十四卷二十册。另外,《饶宗颐新出土文献论证》收录《饶宗颐二十世纪学术文集》未收的许多论文,其中有不少皆是从新出土文献研究早期文学的。[8]2000年以前饶先生研究中国文学相关问题的学术论著,基本收录在《饶宗颐二十世纪学术文集》第十一卷“文学”、十二卷“诗词学”与第十四卷“文录、诗词”。但是,在此书各卷各册中,都有与文学研究相关的内容。比如,卷一“史溯”有早期神话传说的相关论文。卷二“甲骨”、卷三“简帛学”有许多由古文字引发的先秦文学论题。卷五“宗教学”涉及古代宗教文学。又如涉及敦煌文学就在第八卷“敦煌学”,涉及词集考,则在第十卷“目录学”。有些论文兼有不同学科性质,故被同时收入不同卷中。如《从云梦腾文书谈秦代文学》既收入第三卷“简帛学”,又收入第十一卷“文学”。此书之分卷颇有不足,固然有编者的问题,也因为饶先生涉及学科非常广泛,又互有交叉,的确难以明确按现代的学科来划分。

[1]饶宗颐述,胡晓明、李瑞明整理:《饶宗颐学述》,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64页。
[2]《饶宗颐学述》,第90-91页。
[3]《饶宗颐二十世纪学术文集》卷十一,台北:新文丰出版有限公司2003年,第852页。下引此书简称《学术文集》,只注卷数与页码。
[4]《学术文集》卷五,第743页。又参见《学术文集》卷五,第751页,《南戏戏神咒“啰哩嗹”之谜》。
[5]《学术文集》卷十一,第920页。
[6]《固庵文录》后序,饶宗颐:《固庵文录》,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279页。
[7]引自胡晓明著:《古典今义札记》之《风雪夜行人》,深圳:海天出版社2013年版,第111页。
[8]沈建华编:《饶宗颐新出土文献论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9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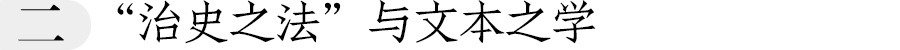
饶先生既说“一切之学必以文学植基”,同时又相当重视史学方法,喜欢用研究历史的眼光和方法来研究文学。《文辙小引》说:“念平生为学,喜以文化史方法,钩沉探赜,原始要终,上下求索,而力图其贯通;即文学方面,鉴赏评骘之余,亦以治史之法处理之。”[1]他在晚年访谈录中进一步解释道:
“以治史之法处理之”,必须从纵横两个方向加以理解。一个是时间,一个是空间。时间与空间不能分割。一般来讲,政治文化史,只是注重时间的演变,忽略空间,这是个缺陷。[2]
可见“治史之法”就是把所有学术问题放到具体的时间与空间及其有机联系中去考察。他研究作品往往从考据史实入手,考证时、地背景,还原历史,探讨作者处于何等现状与心态、写作因缘以及相关的人与事,研究作者写作受到前人何种影响,对后人又产生什么影响。“以治史之法处理之”的好处,就是言必有据,论而可信。饶先生许多文学研究论文,如《楚辞地理考·高唐考附伯庸考》《芜城赋发微》《虬髯客传考》《论顾亭林诗》《司马相如小论——非常之人与非常之文》《论庾信哀江南赋》等等,致力于揭示作品所涉时、地、人、事,可视为一种特殊历史研究。他的专著中,如《楚辞地理考》《清词年表》等也兼具历史学性质。
饶先生认为,任何文本都是历史性的,文本研究也应该“以治史之法处理之”:“主要是一个text。一个本,也可以说是一个源。就小的范围看,是本文,或者文本,就大的范围看,是本源。一定要追溯到那个源。这是我做学问的目标。”[3]每一文本,必寻其出处,考察源流,辨其真假。这方面,目录学有极大的帮助。饶先生说:“我的很多学问的开展,第一把钥匙正是目录学。”[4]但他的目录学又有自己的特色:“我的目录学是开发式的目录学。由此及彼,进入问题;由一个文献系统到另一个文献系统的展开,一路一步地爬梳过去。”[5]在文学研究上,饶先生著有《楚辞书录》《词集考》《远东学院藏唐宋墓志目》等目录学专门著作。他考察文学及观念发展,往往也是从目录学角度来展开的。如《中国文学在目录学上之地位》一文中认为,“目录学本身的任务,是讨论典籍分类之专门学问,我们可以从历代典籍类别,看出某一种学问演进的过程。”[6]从目录书分类系统,可以看出中国文学变迁的大势与文学观念的演进,这在中国文学史研究上,应该是一项重要的课题。
饶先生的研究是建立在文本细读基础上的。他为了写作《楚辞地理考》,看了一千多种志书。为了编《全明词》,遍读台湾所存明人文集及日本内阁文库、哈佛图书馆善本书库中明人的相关文献。[7]他曾拟高似孙《选诗句图》而作《宋词采骚摘句图》[8],此摘句图选取宋人采用《离骚》意趣之词句,共摘选苏轼、晏几道等近百位宋代词人的“采骚”词句。这种摘句图的研制,是建立在文本细读的工夫之上的。编制《宋词采骚摘句图》除了需要熟悉《离骚》,还要遍读全宋词文本,并对其词意进行体会研判,才能从中摘出“采骚”词句来。“摘句图”是中国古代一种特殊的谱图式文学批评方式。《宋词采骚摘句图》从一个角度反映出《离骚》对于宋代词人的影响。比如,从此图可以看出,辛弃疾是用《离骚》句意最多的宋代词人,可以看出辛词与《楚辞》之特殊关系。有此文本功夫,饶先生才敢下此独断之语:“南宋词家,最喜欢用《楚辞》的字句,和摹仿《楚辞》文体的,要算辛弃疾。”[9]
细读文本,从文本中发现内证,是饶先生之所长。关于陆机《文赋》创作年代,逯钦立先生曾有周密考证,已得出陆机晚年所作的论断。但饶先生别出手眼,从《文赋》与陆机其它作品的文本关系出发,从文本内证角度去证明此论断。在《论〈文赋〉与音乐》一文中,饶先生提出:“《文赋》首段内暗嵌陆士衡所作诸赋之名。”《文赋》首段:“遵四时以叹逝,瞻万物而思纷。悲落叶于劲秋,喜柔条于芳春。心懔懔以怀霜,志渺渺而临云。咏世德之骏烈,诵先人之清芬。”饶先生认为,其中至少嵌有陆机平生所作《感时》《叹逝》《述思赋》《行思赋》《思归赋》《愍思赋》《浮云赋》《白云赋》《祖德》《述先》等赋之名与相关辞句,由此得出结论:“《文赋》自是其晚岁所作,故开首总述平生各赋,檃括为言。由此一端,足证《文赋》决非年二十所作。”[10]
精彩的文本分析,既基于博览之力,又须有雅鉴之功。清代词人项鸿祚(莲生)曾谓:“不为无益之事,何以遣有涯之生。”此语经过谭献《箧中词》品题,成为家弦户诵的名句。在《词与画——论艺术的换位问题》一文中,饶先生指出,这句话原出自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卷二:“妻子僮仆切切嗤笑,或曰:终日为无益之事,竟何补哉?既而叹曰:若复不为无益之事,则安能悦有涯之生?”[11]在项鸿祚之前,浙西词人厉鹗已套用过张彦远语:“张彦远云:‘非为无益之事,又安能悦有涯之生。’;海内不乏雅流,得此亦悦生之一助云。”[12]然后饶先生分析项莲生对古语的改引:
项氏画龙点睛地把“悦”字改为“遣”字,“何以遣有涯之生”比“安能悦有涯之生”来得多么令人动容,句子活起来了,从此遂成名句。[13]
这就不但指出此语的出处与传播源流,又指出其所以传诵的艺术原因。这种文本细读,兼用治史之法与鉴赏之法。
饶先生对文本的考据,往往采用多学科的知识和方法。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指出,岳飞孙子岳珂所著《鄂王家集》,没有收入岳飞《满江红》一词,认为此词是“伪作”“赝本”[14]。此后,夏承焘先生《论词绝句》:“黄龙月隔贺兰云,西北当年靖战氛。《玉海》舆图曾照眼,笑他耳食万词人。”其题解说:“岳飞北伐,目的在直捣吉林的黄龙府。而今传岳飞的《满江红》词,却有‘踏破贺兰山缺’句。贺兰山在河套西边,时属西夏,当时西夏和南宋并无战象。王应麟编的《玉海》载有西夏贺兰山图。王氏南宋末年人,还见此图,岳飞决不致于无此舆地常识,分不清贺兰山和黄龙府的。”又说:“明朝弘治年间,大将王越曾破鞑靼入侵军于贺兰山,明人刊岳飞《满江红》词于西湖岳坟,碑阴记年是弘治年间。作者疑《满江红》词或是王越幕府文士所作,托名岳飞以鼓舞士气。”[15]当时,争议者甚多。其中饶先生《贺兰山与〈满江红〉》一文对伪作说的反驳较有力量。[16]他首先从版本目录学和文献学角度,用宋人所引用岳飞诗之文献,有力地证明“飞之作品,不入于《鄂王集》者多矣”,故不能以《鄂王集》未收而否定岳飞《满江红》的著作权。又从文学创作特点指出:“词中用贺兰山字眼,乃借用回纥地名,不得谓其昧于地理也。”更重要的是用大量文献与石刻来说明:“王越平贺兰山,实在弘治十年冬。此词在景泰以前,早已流行。”[17]其中有一段文字:
夏氏因断此词为弘治间人拟托之作,实不可从。今汤阴岳王庙内肃瞻亭院壁上有天顺二年春二月庠生王熙书《满江红》,末句作“朝金阙”。余于一九八七年九月,从安阳至汤阴,曾摩挲此石刻,流连久之。[18]
这是颇带诗意的文本实地考察。饶先生对《满江红》的文本考据,得心应手地采用目录学、版本学、文学批评和田野考察多种方式,在此词真伪的学术讨论中,显得比较独特而有力。虽然此考据仍不能完全肯定《满江红》为岳飞所作,但至少有力质疑了余嘉锡、夏承焘先生所提出《满江红》为明人“伪作”的几条依据,从而维护《满江红》为岳飞所作之旧说。

[1]《文辙小引》,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91年版,《文辙》卷首。
[2]施议对编纂:《文学与神明——饶宗颐访谈录》,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年版,第30页。
[3]《文学与神明——饶宗颐访谈录》,第21页。
[4]《饶宗颐学述》,第48页。
[5]《饶宗颐学述》,第78页。
[6]《学术文集》卷十一,第829页。
[7]《饶宗颐学述》,第77页。
[8]《学术文集》卷十一,第412页。
[9]《学术文集》卷十一,第376页。
[10]《学术文集》卷十一,第495-496页。
[11]张彦远撰:《历代名画记》,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88页。
[12]《赏延素心录题辞》,厉鹗著、董兆熊注:《樊榭山房集·文集》卷八,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831页。
[13]《学术文集》卷十三,第347-348页。
[14]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卷二十三,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1452页。
[15]夏承焘著,吴无闻注:《瞿髯论词绝句》,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30-32页。
[16]《学术文集》卷十二,第253页。
[17]《学术文集》卷十二,第268页。
[18]《学术文集》卷十二,第264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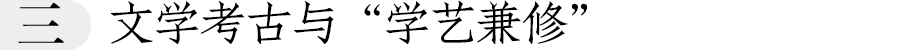
杰出学者都有自己独到之处。饶先生非常重视和擅长利用新出土或新发现的文献来研究文学,互相印证,富有开拓性。饶先生说:“我很强调‘三重证据法’(指田野考古、文献纪录和甲骨文三方面的资料),一定要把考古遗存同传世文献结合起来进行考察和研究。”[1]他有意识地把文学与考古学结合起来,这或可以称之为“文学考古”。尤其是《楚辞》考古方面,他在上世纪70年代初期已导夫先路。根据学者统计,饶先生《长沙楚墓时占神物图卷考释》《荆楚文化》《长沙楚墓帛画山鬼图跋》三文,在20世纪《楚辞》考古方面论著中,发表时间位居前三。[2]1972年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出土竹简中,发现《唐勒赋》。饶先生《唐勒及其佚文——《楚辞》新资料》[3]一文,不但研究《唐勒赋》,并且与宋玉《大言赋》《小言赋》的真伪问题联系起来,引发学界对此问题注意和讨论。90年代,不少学者发表论文,把《唐勒赋》与宋玉赋联系起来研究,基本认定《大言赋》《小言赋》的真实性。[4]1993年10月,郭店楚简出土,轰动了学术界。多数学者利用郭店楚简研究中国哲学史和思想史,饶先生则还利用来研究中国早期文学,他撰写《郭店楚简与〈天问〉》《诗言志再辨——以郭店楚简资料为中心》《〈神乌傅(赋)〉与东海文风》《楚简〈诗说〉的理论及其历史背景》等多篇论文,大大拓展对早期文学的认识。其中,《郭店楚简与〈天问〉》一文,在郭店楚简中,找到可以阐释《天问》中“地何故以东南倾”一语的相关文献,为理解《天问》知识背景提供借鉴。[5]
由于秦祚短暂,秦代文学文献向来很匮缺。1975年在湖北云梦睡虎地发现大批竹简,1976年饶先生在巴黎看到相关材料,即敏锐地注意到其研究价值。该年10月19日他在香港大学做了专题演讲《从地下材料谈秦代文学》,谈到这些新材料中,有一种是秦始皇二十年一位叫腾的南郡太守的文书,可以补充秦代文学研究史料。[6]他据此撰写的《从云梦〈腾文书〉谈秦代散文》说:“《腾文书》是一篇很好的散文,笔调很像韩非子的句法,行文很精采,念起来有铿锵的节奏,是水准非常高的一篇散文。这居然出于一个南郡太守的手笔。”“这篇文告完全站在法家立场说话,和韩非子的文章十分接近……文章写得非常好,这是很重要的发现。”[7]饶先生对腾文书艺术价值的高度评价,不一定准确,但其眼光的确极为独到:他在出土文献中首次发现其他文学史家没有注意的新材料,并且把这些新材料和韩非子文章加以比对,从而论证秦代文章的一些风格特点。
《汉书·艺文志》取《七略》之说:“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之所造也。”此前,许多学者都把《汉志》作为研究“稗官”的最早文献,以“稗官”之称始于汉代。但饶先生从新出土文献发现新问题。《秦简中“稗官”及如淳称魏时谓“偶语为稗”说——论小说与稗官》一文,发现云梦秦简秦律中即见到“稗官”一词,从而考据其原始意义,绝不是始于汉代,而是有更久远的出处。“可见《汉志》远有所本,稗官,秦时已有之。”[8]他进而研究先秦时期稗官与小说、偶语的关系,把先秦文学研究推进了一步。
孔子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历来都认为“一言以蔽之”指的是孔子对《诗经》总体风格的概括。饶先生对上博简《诗序》做出解读,从而得出完全不同的见解:
“向来我们对“一言以蔽”的涵义,在于概括三百篇,现在读了竹书《诗序》,用一言来断诗的涵义,几乎每一篇都可以用一字来下断语,像《关雎》之改,《樛木》之时,《汉广》之知,《鹊巢》之归,《甘棠》之保,《绿衣》之思,《燕燕》之情,是最好的例证……这十分明显,用一言以蔽之,是孔子采取“易简而天下之理得”的最方便的读诗法,施用于《诗经》全部,或每一篇都可以用之。[9]
这就是说,“一言以蔽之”意思是,《诗经》每一篇“都可以用一字来下断语”,这是孔子提出来“最方便的读诗法”。这是迥异于以往的新说,虽非定论,但的确很有启发性。
把学术研究与艺术创作结合起来,这是饶先生传承中国学术传统的独特处。他认为:“古人说‘不通一艺莫谈艺’,我觉得是很有道理的,写作诗词和评论诗词常常可以互为体用。”[10]从文学批评角度看,具有创作经验的批评家对文学艺术的体验往往更深切。饶先生赞成“道通为一”,认为诗、书、画以及理论评论之间都有相通之处,可以互相借鉴。“这几种艺术在中国都是互用的,我想西洋也有这种情况,这是人类共同的一个想法:换位。”[11]饶先生明确地说:“我的目标是学艺兼修。”[12]他是学者,也是诗人、词人、辞赋家、古文家、书法家、画家、音乐家,在学、艺两方面都达到罕有高度。饶先生有雅人深致,故其研究往往能打通文学与艺术边界,拓展和加深文学研究。
饶先生喜欢沉吟把玩古诗,追摹古人,唱和古人之作,曾和谢灵运诗36首(收入《白石集》)、和阮籍诗82首(收入《咏怀集》),遍和清真词127章(编为《晞周集》),对古人体会更加亲切,对其批评也更有独见。饶先生又和姜夔词,编入《固庵词》[13],对白石词独有会心之论。王国维曾批评姜词“二十四桥仍在,波心荡,冷月无声”“数峰清苦,商略黄昏雨”“高树晚蝉,说西风消息”等词的缺点是“隔”。饶先生在《人间词话平议》文中则认为,“此其妙处,正在于隔”:
予谓“美人如花隔云端”,不特未损其美,反益彰其美,故“隔”不足为词之病……词者,意内而言外,以隐胜,不以显胜。寓意于景,而非见意于景。[14]
历来多称白石词“清空”,而饶先生《姜白石词管窥》一文,特别从姜夔的书法、琴律艺术入手,认为“骨力”与“风神”,是姜夔词、书与琴一致的艺术追求:“白石的书法要下笔劲净,正在练骨上着力,于词亦有同然。他论书主风神,以疏为贵,又要时出新意;他作词亦循着这条路径。”“所以我欲拈出‘风骨’二字,来评白石的词,较之‘清空’似更接近。”[15]若没有对词艺与书艺、琴艺的深刻体悟,是不可能提出这些独特见解的,故饶先生说:“我这些观点都是很细微的感受,如果没有唱和的经历是感知不到的。”[16]
饶先生善画,又擅长从绘画、图像角度来研究文学,写出《文选序“画像则赞兴”说——列传与画赞》《〈楚辞〉与古西南夷之故事画》《词与画——论艺术的换位问题》《从“睒变”论变文与图绘之关系》《楚缯书之摹本及图像——三首神、肥遗与印度古神话之比较》等大量论文。《诗画通义》一文揭示诗与画的微妙关系:“天下有大美而不言,能言之者,非画即诗。画人资之以作画,诗人得之以成诗;出于沉思翰藻谓之诗,出于气韵骨法谓之画。”[17]并从“神思”“图诗”“气韵”“禅关”“度势”“伫兴”六个方面,对诗画的相互体用探秘发微,深化了“诗画本一律”这一古老命题。又如利用图像学来研究文学。马王堆汉墓出土的《社神图》[18]当时已有不少研究者,而饶先生《马王堆新出〈大一出行图〉私见》一文则据此讨论古代“图诗”“图赞”文体,并与《楚辞·远游》合证,角度非常独特而新颖。[19]饶先生还利用图像研究古代神话。历来以为盘古之说最早出自三国时徐整《三五历记》,而饶先生《盘古图考》从一则盘古图新材料的记载,得出结论:“以盘古作图,汉末蜀中已流行之,则盘古之神话,最迟必产生于东汉。”[20]这是对盘古神话产生年代的新见解。
楚辞研究历来都是显学,但饶先生仍凭借其特殊的艺术修养,开创出新境界。1957年他在德国第十届汉学会议上,提交《〈楚辞〉与词曲音乐》一文。他与多数楚辞学者的差别,在于他把艺术体验与文学研究完美地结合起来。饶先生说:“写作《楚辞与古琴曲》,分析《离骚》‘以声写情’的艺术手法,无不得力于我对古琴的熟玩。”[21]他善音乐,能演奏古曲,所以注意到楚辞与琴曲的关系。他为了撰写“《楚辞》与古琴曲”部分内容,“曾下了半载的工夫,弹过数十遍,对它颇有体会”。文中写演奏《离骚》琴曲的体会:
“长叹掩涕”段,双弹再作,描写涕泣之声;而飞猱、引上、退复,则表示叹息。《回车延伫》段,先以散声之滚、拂,状车马驰骤;未叠用虚点、虚罨、及搯、撮,凡再作三作,把屈原那一种徘徊返顾,不忍远离的悲伤怨慕的情绪,活现出来……[22]
在论文中,插入自己弹奏《离骚》古琴曲体会,这的确很独特,也只有“学艺兼修”才具备的绝招。饶先生又说:“因为我懂音乐,所以我能够提倡词乐研究。从来研究词学的人,往往不太留心词乐,一方面他们也不太懂得怎样谱曲。”[23]他擅长演奏古曲,从而留意到“词乐”这个颇受忽视的独特的艺术领域。他认为,此前学者所注意的问题其实只是“文学史上词与音乐的关系研究,并不是真正的‘词乐研究’”。[24]1958年,他与赵尊岳等合作出版《词乐丛刊》,写了《白石旁谱新诠》《陈澧越九歌译谱》《乐府浑成集残谱小笺》《玉田讴歌八首字诂》诸论文,“为词学中‘词乐研究’这个领域奠下了一个基础”。[25]此后,他对敦煌曲的研究也非常得力于对音乐的熟悉,从而开拓了一个新的艺术领域。

[1]《饶宗颐学述》,第86页。
[2]参考陈桐生:《二十世纪考古文献与楚辞研究》,载《文献》1998年第1期
[3]原载九州大学《中国文学论集》第九号。收入《学术文集》卷十一,第57-63页。
[4]谭家健《〈唐勒〉赋残篇考释及其他》,《文学遗产》1990年第2期。汤漳平《宋玉作品真伪辩》,《文学评论》1991年第5期。
[5]《学术文集》卷三,第21-24页。
[6]据郑炜明等:《饶宗颐教授著作目录三编》,济南:齐鲁出版社,2014年。
[7]《学术文集》卷十一,第923-931页。
[8]《学术文集》卷三,第60页。
[9]《兴于诗——〈诗序〉心理学的分析》之一《“一言以蔽之”的读诗法》,载《饶宗颐新出土文献论证》,第201页。
[10]《饶宗颐学述》,第94页。
[11]《饶宗颐学述》,第99页。
[12]《文学与神明——饶宗颐访谈录》,第2页。
[13]如《法曲献仙音》(双桨萍分)、《角招》(晚烟瘦)、《凄凉犯》(冰弦漫谱衡阳雁)等,《学术文集》卷十四,第572、575、583页。
[14]《学术文集》卷十二,316页。
[15]《学术文集》卷十二,234-235页。
[16]《饶宗颐学述》,第95页。
[17]《学术文集》卷十三,第342页。
[18]此图名称有争议,有《社神图》《神祗图》《避兵图》等,饶先生称为《大一出行图》。
[19]《学术文集》卷十三,215页。
[20]《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86年第1期。
[21]《饶宗颐学述》,第96-97页。
[22]《学术文集》卷十一,399页。
[23]《饶宗颐学述》,第97页。
[24]《饶宗颐学述》,第97页。
[25]《饶宗颐学述》,第97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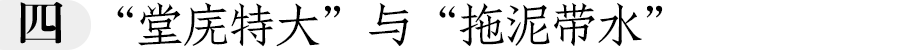
饶先生曾说:
中国文化本来就是文、史、哲打通的精神生命,一方面是要把握住天人合一的文化大义,一方面要经、史、文、哲互为表里,这样贯穿起来通观全部,学问的背后才能有全体、整幅的民族文化精神生命作支撑,这样“堂庑特大”,才能到达“通儒”的境界。[1]
他在治学上呈现出宏大的气象和格局,正可当“堂庑特大”四字。钱仲联先生曾把饶先生与王国维、陈寅恪先生作比较:“今选堂先生之学,固已奄有二家之长而更博。”[2]以饶先生以优越之治学条件和百岁之寿命,比二家更“博”,是可以肯定的。[3]饶先生学术的“堂庑特大”,除了其过人之天赋,还基于其特别的认识论,这就是“超于象外”:
我一向观世如史,保持着“超于象外”的心态,从高处向下看,不局促于一草一木,四维空间,还有上下。这是我个人的认识论。
贯通上下古今,贯通万界万物,才能大彻大悟。[4]
贯通时空,大彻大悟,这是何等的气魄!饶先生立论极高,他探讨的是人类精神史,所谓“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在天、地、人之间立论。从人类文化历史高度审视国内与域外的文化交流史料,以开阔视野来研究一切对象的内涵和起因,而不局限于一时一地。
饶先生治学“堂庑特大”,不但因为广博,还因为他有一种自觉的系统意识。他曾比较中、西方汉学的某些特点与缺陷:
外国汉学家……讨论汉学上的历史问题,每每方才认识几桩事实,即喜欢企图建立一套理论拿来作全面的解释,有时不免“屈事以就理”。而中国人对自己的历史认识,似太过于注意一些零碎的事实,不敢轻易去作概括性的系统理论,好像胆识有点不够。[5]
他认识到中国学者的缺陷,所以有意在这方面表现出特别的“胆识”。令人惊佩的是,他越到晚年,这种学科意识越发健旺,越发自信,而绝无衰飒气象与心态。比如,倡导建立楚辞学、华学、新经学。1978年,饶先生提出建立“楚辞学”。[6]虽然此前已有人用过“楚辞学”三字[7],但饶先生的“楚辞学”和传统的“楚辞研究”不同之处,在于倡导采用新的治学方法、新材料和新观念,更为系统地研究文化史问题。如《楚辞》与考古学、地理学、神话学、音韵学、音乐、绘画、域外文化等关系问题。1997年,饶先生创办学术刊物《华学》,主张用“华学”代替“国学”或“汉学”指代中国传统文化。在他看来,“国学”这个名词无法作为中国文化的独有称谓,因为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国学”。如果用“汉学”指代中国传统文化,容易跟清儒的“汉学”“宋学”概念混淆。西方汉学家往往带着西方人观点来看中国文化,使用“汉学”更不准确。[8]2001年11月,他在北京大学百年纪念论坛上作题为《新经学的提出——预期的文艺复兴工作》专题演讲,提出在21世纪中国重建经学的理论框架。[9]2013年,他再次提出:“21世纪是重新整理古籍和有选择地重拾传统道德与文化的时代,当此之时,应当重新塑造我们的‘新经学’。”[10]仍念念不忘建立“新经学”。
饶先生“堂庑特大”的学术境界,还在其强烈的创新性。他在学术上就像一位志在开疆拓土的将军,不像一般学者,一辈子只钻研某个时代,某个领域,甚至某本书。他是极有创作意识和欲望的学者,每每看到新材料、新文献,即启动广博的积累,迅速进行比对、综合,从各个方面和角度进行分析,从而产生新看法。有人总结,饶先生在治学上有50项“第一”[11]。对此类统计,得意忘言可也。饶先生在文学研究领域里也有许多开创性的工作。他所编著、辑录的《楚辞书录》《词集考》《全明词》《清词年表》等都具有首创性。在学术研究上,独特性有时比“第一”更重要。1956年,饶先生编著《楚辞书录》[12]是第一部楚辞目录学著作,其值得注意之处还在于体现出和传统目录学不同的眼光。比如“图像”部分辑录自宋代至民国以来《楚辞》作品之图像,并详加考证,可以说涉及文学图像学以及诗与画关系问题,很有新意,也很重要。[13]“译本”部分收录包括德文、英语、法文、意大利文、日文的《楚辞》文献,[14]这种外文目录反映出中国文学经典之外译与传播情况,传统学者未必有此眼光,或未必有多种外语能力。
近代以来,西学东渐,学者多注意到西方文学对中国之影响。直到晚近,学界才比较留意中国文学在域外的传播和影响。随着中国的崛起,这个问题越显重要。饶先生在60年代已注意到这个问题。《清词与东南亚诸国》一文选题非常独特:“有清一代,倚声之业,如日中天。作者綦众,凌越前古……雅声所被,覃及四裔。”[15]当时研究清词的学者很少,对清词在海外影响与传播的研究,则基本是空白。饶先生在1939年佐叶恭绰选辑《清词钞》,就开始留心清词,1969年出版《清词年表》,对清词与词人的情况比较熟悉。此文讨论清代词人在东南亚之作与东南亚本土词人的创作,涉及的国家有越南、缅甸、暹罗、新加坡。文章虽然简短,但确实显示一种新的学术眼光和视野。随着时间的推移,相关话题并没有过时,其重要性反而日益显示出来。
饶先生提出,治中国文化宜除二障:“一是西方框框之障,二是疑古过甚之障。”[16]他有强烈的本土文化意识和自信心,反对用西方概念强行比附中国文学,比如《连珠与逻辑——文学史上中西接触误解之一例》,反对用“连珠”这种文体来比附“逻辑”。他批评说:“自从中西思想接触以来,外来名词许多径从日本吸取,国人无条件接受而不加以仔细探讨。”[17]但另一方面,饶先生具有开阔的国际视野,善于用新方法与新材料来丰富传统学术,使之获得新的发展。《“天问”文体的源流——“发问”文学之探讨》(1976年)是文学研究的经典之作。文章开宗明义:“从比较文学的观点来考察,这种‘发问形态’的文学作品,自有它的源远流长的历史。”[18]饶先生认为:“《天问》在文学上的价值,于《楚辞》中向来被认为最低,但它却有最特出的一面,为他篇所不及。”[19]“如果我们放开视野,把世界古代文学上的具有发问句型的材料,列在一起作出比较,以及从同样文体推寻它的成长孳生的经过,作深入的探讨,这种研究的方向,亦可以说几乎接近Northrop Frye所说的‘文学人类学’的范围了。”[20]饶先生认为,“发问文学”不但在中国文学史上形成历代拟作传统,而且世界上一些最古老的经典,如印度《梨俱吠陀》、古伊朗的Avesta和《圣经·旧约》都有类似的发问诗歌。他从比较文学的角度来讨论《天问》,不是为了罗列材料,而是为了“说明人类写作的共同心理”。从古今中外作品中,看到全世界早期文明普遍有一种独特的“发问”文体。在这个基础上,他提出一个重要问题就是“文学人类学”,探讨人类学与文学的关系。“文学作品是人类精神的产物,人类学领域中的奇葩异卉……屈原的《天问》,不特是卓绝的文学产品,亦是无可忽视的人类学上的素材。”[21]到20世纪末,“文学人类学”才在中国大陆学术界较为兴盛,但饶先生在70年代就采用这种说法,令人感佩。
饶先生“堂庑特大”的学术格局和他读书、治学的“贯通”方法相关。他说:
我以为,读书须贯通,做学问也须贯通。长期以来,我养成了一种习惯,就是拖泥带水。这一习惯,说得文雅一点,就是一种联系,将十万八千里以外,看似毫无牵连的问题集中一起,进行探究。所以,面铺得较宽。[22]
“贯通”是饶先生的特色,也是其自觉追求。贯通与专精往往是一对矛盾体。现代学者大多是在特定的学科分类背景下进行研究,专攻某个领域。饶先生的研究全凭兴趣,信马由缰,自由发挥,所以“面铺得较宽”。从特定专业的专家看来,其研究未必都很精深。但是,学科贯通者的眼光和方法,自有优势。饶先生的头脑似乎是一个由各种专业数据库合成的超大数据库,凡遇一问题,即能迅速、自然地从各个不同学科领域的角度去考虑,从古今中外的文献中搜索、比对。不同学科贯通融合,互相碰撞产生智慧之光,或者起某种“化学作用”,合成新的成果,这是专守一业者所无法做到的。饶先生说:“我的学问很杂,从上古到明清,从西亚到东亚,都有涉猎。这当中有一个好处,就是视野开阔了,联想层面就多,作比较也就客观、亲切了。”[23]联系的方法与联想的思维,正是他的特长。饶先生论文的标题制作便反映出这种“拖泥带水”的研究特点,他非常喜欢使用“某某与某某”为标题。如《中国文学史上宗教与文学的特殊关系》《屈原与经术》《楚辞与词曲音乐》《<楚辞>与戏曲》《<楚辞>与古琴曲》《论<文赋>与音乐》《汉字与诗学》《元典章与白话文》《“言路”与“戏路”》《词与禅》《词与画——论艺术的换位问题》《清词与东南亚诸国》。这些“与”字句式,具有很强的学术联想力与学术张力。有些论文虽然不是这种题目,但其内容仍是这种思路。如《中国古代文学之比较研究》一文论及五个问题:名号与文字、诅盟与文学、史诗与讲唱、诗词与禅悟、文评与释典。这些问题之间,按他自己的说法:“相去九万八千里,拉扯得很远……我只希望在文学解悟上,和大家一同找出‘向上’一路。”[24]此篇文章涉及文学发展史、文学批评史的许多重要问题,显现出宏大的学术气魄与联想力,给人以向上一路的启示。
饶先生所说的“联系”或者“拖泥带水”,听起来似乎简单,其实极为艰难。“联系”首先需要具备敏锐的学术眼光与识力,能找到不同研究对象之间的内在联系,还需要具备广博的学科知识、艺术修养以及古今中外语言能力。比如《穆护歌》是隋唐时代乐府诗,饶先生《〈穆护歌〉考——兼论火祆教、摩尼教入华之早期史料及其对文学、音乐、绘事之影响》一文引证近百种文献指出:“牧护、穆护原为祆教僧之称。由于祆教之普及,唐宋以降,穆护已成为一通名。故以其所唱之歌,通称为《穆护歌》。”[25]并由此研究火祆教入华的早期史料,涉及中外交通史、文学、宗教、艺术、语言等多学科领域的偏题与难题。这种选题是只专攻某学科的学者所无法想出来的,或者没有能力完成的。

[1]《饶宗颐学述》,第91页。
[2]《选堂诗存·钱序》,《学术文集》第十四卷,第339页。
[3]多年前,饶先生就曾说:“清末两位大学者——龚自珍和王国维,与他们比较,自不敢当,所不同的是,我比他们长命。龚自珍只活到四十九岁,王国维五十岁。以他们五十岁的成绩,和我八九十岁的成绩比较,是不够公平的。”《文学与神明——饶宗颐访谈录》,第17页。
[4]《文学与神明——饶宗颐访谈录》,第30页。
[5]《饶宗颐学述》,第122页。
[6]《学术文集》卷十一,第23页,《楚辞学及其相关问题》。
[7]徐英《楚辞札记》卷一即用“楚辞与楚辞学”之名。南京:钟山书局,1935年版,第2页。
[8]郑炜明:《饶宗颐主张用“华学”取代“国学”》,载2014年7月8日人民网强国论坛。
[9]收入《学术文集》卷四,第7页。
[10]饶宗颐:《中国梦当有文化作为》,《人民日报》2013年7月5日。
[11]陈韩曦:《饶宗颐学艺记》,广州:花城出版社,2011年版,第240页。附表:“饶宗颐教授在学术研究上的50项第一”。此前胡晓明在《最后的通人:饶宗颐》一文已有相关说法,载《社会科学报》2002年11月28日第7版。
[12]《学术文集》卷十一,第211页。
[13]《学术文集》卷十一,第275页。
[14]《学术文集》卷十一,第289页。
[15]《学术文集》卷十二,第360页。
[16]《文学与神明——饶宗颐访谈录》,第25页。
[17]《学术文集》卷十一,第947页。
[18]《学术文集》卷十一,第35页。
[19]《学术文集》卷十一,第52页。
[20]《学术文集》卷十一,第53页。
[21]《学术文集》卷十一,第52页。
[22]《文学与神明——饶宗颐访谈录》,第7页。
[23]《饶宗颐学述》,第90页。
[24]《学术文集》卷十一,第828页。
[25]《学术文集》卷十二,第29页。

阮元说:“学术盛衰,当于百年前后论升降焉。”(《十驾斋养新录〉序》)要准确、恰当地从学术史角度评价饶宗颐先生的学术成就、地位与影响,现在为时尚早,这需要较长时段的历史检验。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自20世纪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经过广泛西方化、专业化的影响之后,饶宗颐继承王国维、陈寅恪先生等前贤,走出一条在现代学术与国际汉学背景下回归中国学术传统的独特之路。他努力在“博古通今、中西融贯”这个层面上回归中国学术传统。他在学术史上的得失轩轾,大致缘于此。
如果说,现代学术研究已经处于高度的学科专业化,饶先生的治学方式则更像中国传统学者,于学无所不窥,经史子集四部兼治。饶先生曾幽默地自称在学术上“无家可归”[1],他以一人之力,涉及古今中外众多学科领域,可谓“博古通今、中西融贯”。当然,就其特定领域与具体问题的研究而言,论证未必都周全严密,结论未必皆精当不灭。但他的研究容或有粗疏,决无凡庸平浅;容或有零碎,决无框框套套。
饶先生在学术研究上,快意于开疆辟土,而不经意于屯垦戍边。他的治学特色是创造性优于严谨性。他敢为天下先,“先”并不等于典范。学术史上,有许多“前修未密,后出转精”之例。饶先生一些研究,尤其是对新发现的材料,往往有感即录,敏锐而简要地提出问题,点到为止,近乎读书札记,吉光片羽之中,包含闪光的思想。后来有些问题得到深化或修订,有些则由于兴趣转移或无暇顾及。另外,饶先生喜欢用大题目,往往题大而文小,题目富有启示性,论证方面则未能尽意。这些都给后学者留下许多可供深入研究的空间。比如,“诗妖说”在中国古代是一个很重要的命题,饶先生《诗妖说》[2]一文在杜文澜《古谣谚》所载文献基础上,补充抄录相关几条材料,并没有更深的系统阐释,虽然只是寥寥数百字,但提出一个重要的学术问题,即神秘文化对古代文学批评的影响。“诗妖”是异常社会状态下所产生的异常诗歌。“诗妖”理论与传统的“诗言志”说的相通处是强调诗歌与政治的直接关系,不同之处在于“诗言志”说把诗看成现实的反映,而“诗妖”说不仅强调诗歌产生的现实基础,更把诗歌看成是现实的先兆。所以,“诗妖”说值得后学者继续深入系统研究。[3]1972年,临沂银雀山汉墓所出土的《孙膑兵法》,其中有《客主人分》一篇。饶先生《释主客——论文学与兵家言》一文指出,“客主”是兵法上的一个术语,然后又指出:“兵家主要观念,后世施之文学,莫切于气与势二者。”[4]此文题目与意义都非常大,因为它揭示了中国文学批评史上“文学与兵法”关系这一重要话题。但是该文只有几百字,虽提出问题,而未加细论。后来者在此基础上可以继续深入研究。[5]
饶先生在学术研究上有些结论是确证,有些只是提出某种可能性或猜想。他很早就注意到佛教对刘勰的影响,1954年他就发表《文心雕龙与佛教》一文,此后,又撰写《〈文心雕龙〉与〈阿毗昙心〉》,认为两书有相通之处:“六朝初期,《阿毗昙心》之学盛行。”刘勰居定林寺,从僧祐学佛经,深于佛理,对此书“当甚熟悉。其撰《文心》此书,亦以‘心’作为书名。虽与《阿毗昙心》之名偶合,未必无‘窃比’之意。为最上法之要解,号之曰心;为文之要解,自亦可号之曰心。”[6]《〈文心雕龙〉与佛教》一文,从几方面研究《文心雕龙》与佛教之关系,并指出:“凡二种不同文化经过接触交流浸灌之后,便可收融会贯通之效。刘氏的《文心雕龙》,正是一绝好例子。”[7]他列举《文心雕龙》和“释氏思想有连带关系”的例证,如认为“刘氏征圣的态度和佛家思想似乎不无关系”,[8]刘勰是从佛教唯心论以立说,故该书命名《文心》,又认为全书体例严密,也受到佛教的影响。还有“带数法的运用”,如《知音篇》标揭“六观”:“这是归纳为若干事类后,用数来统理它,很像佛家术语的‘三观’‘三量’等等……中国古代学者,亦常用这种方法,但没有佛门那样用得区分明细。晋、宋以来,处理佛经界品,便是常用这种‘带数法’的。”[9]这提出一种富有新意的启发性推测,但又很难得到实证,故未能完全让人采信。又如饶先生认为文天祥《正气歌》题目之“正气”一词,源于《楚辞·远游》“求正气之所由”一语[10],这当然可备一说。然孟子倡导“养气”,其“浩然之气”即指正气,正大刚直之气。《孟子·公孙丑上》:“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文天祥《正气歌》:“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下则为河岳,上则为日星,于人曰浩然,沛乎塞苍冥。”从文本来看,《正气歌》对“正气”的描写,应该更接近孟子对“浩然之气”的描述,《远游》受其影响的可能性也许更大。“正气”一词,在古代使用得很多,饶先生提出《正气歌》“正气”一词出于《远游》,此说显得有些随意。
饶先生的中国文学研究,既给后人提供了仰望的典范,也留下许多启迪与空间。他曾说:“我历年来不断提出许多仍待解决的问题,后浪推前浪,有无穷的新领域,正等待后人去耕垦、拓殖。”[11]后学者纪念饶先生最好的方式,就是领略其学术精神与学术智慧,追随其步伐在广袤的学术领域中,继续“耕垦、拓殖”。

[1]引自《时代潮人》2012年第1期《专访港大饶宗颐学术馆研究中心主任郑炜明》。
[2]《学术文集》卷四,214-215页。
[3]参见拙作《论谣谶与诗谶》,载《文学评论》1996年第2期。
[4]《学术文集》卷十一,859页。
[5]参见拙作《古代兵法与文学批评》,载《文学遗产》1998年第6期。
[6]《学术文集》卷十一,1056页。
[7]《学术文集》卷十一,第1070页。
[8]《学术文集》卷十一,第1062页。
[9]《学术文集》卷十一,第1064页。
[10]“(戴密微教授)曩曾与余论及文天祥就义前之《正气歌》,嗣因读《远游》,方知‘正气’二字,实出该篇‘内惟省以端操兮,求正气之所由’句。”《骚言志说》,《学术文集》卷十一,第21页。
[11]郑炜明编:《论饶宗颐》,饶宗颐“跋”,香港: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1995年,第519页。
原载:《文学评论》2018年第四期,原题《饶宗颐的中国文学研究》
【名家简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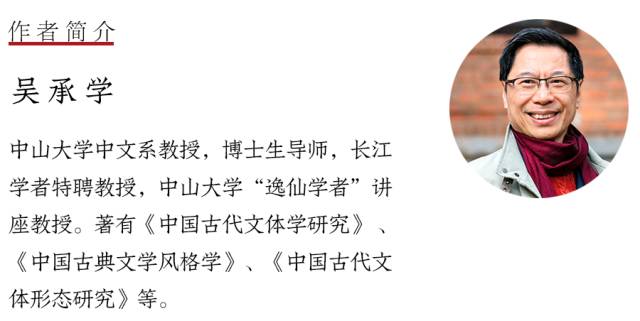
-
【名家文论•吴承学】饶宗颐的意义
2024-06-18 14:31:47 -
【名家文论•刘启宇】赓续中华文脉 推动岭南文化焕发新光彩
2024-06-11 10:32:16 -
【名家文论•文刃】在爱琴海的星光下
2024-06-08 12:13:57 -
【名家文论•林伦伦】韩江之思与广济桥之念——序李英群、邢映纯《潮州有座广济桥》
2024-06-07 15:08:3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