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同文馆由广州将军筹办、粤海关监督衙门主管。其建馆初衷是为粤海关培养精通英语的人才,后来学科范围极大地扩展,目前除了英语之外,还教授法语、日语和俄语,也为满汉世家子弟开设各种门类的西学课程。”
美国医生、传教士嘉约翰(John Glasgow Kerr,1824—1901)于1854年至广州行医,其编撰的《清代广州旅本》中有对广州同文馆的这样一段记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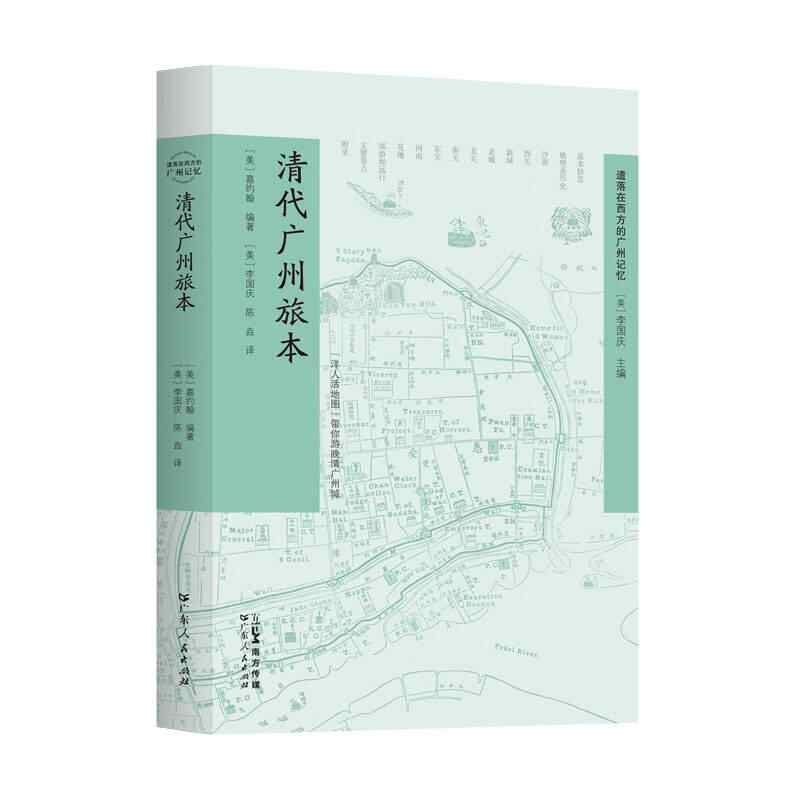
根据《广州市情网》的资料介绍,1862年(同治元年),在恭亲王的倡议下,北京、上海先后办起了同文馆。广州政界对此举深为重视,同治三年(1864)6月,广州将军瑞麟、两广总督毛鸿宾奏请清王朝,依照京沪之例创办广州同文馆。
那么,广州同文馆为何由海关衙门主管?其建立的背景是什么?又发挥了什么作用呢?
同文馆的设立
1850年来华的美国北长老会传教士、曾任京师同文馆总教习丁韪良(William Alexander ParsonsMartin,1827-1916)所著的《花甲忆记(修订译本)》,对同文馆的设立有详细的阐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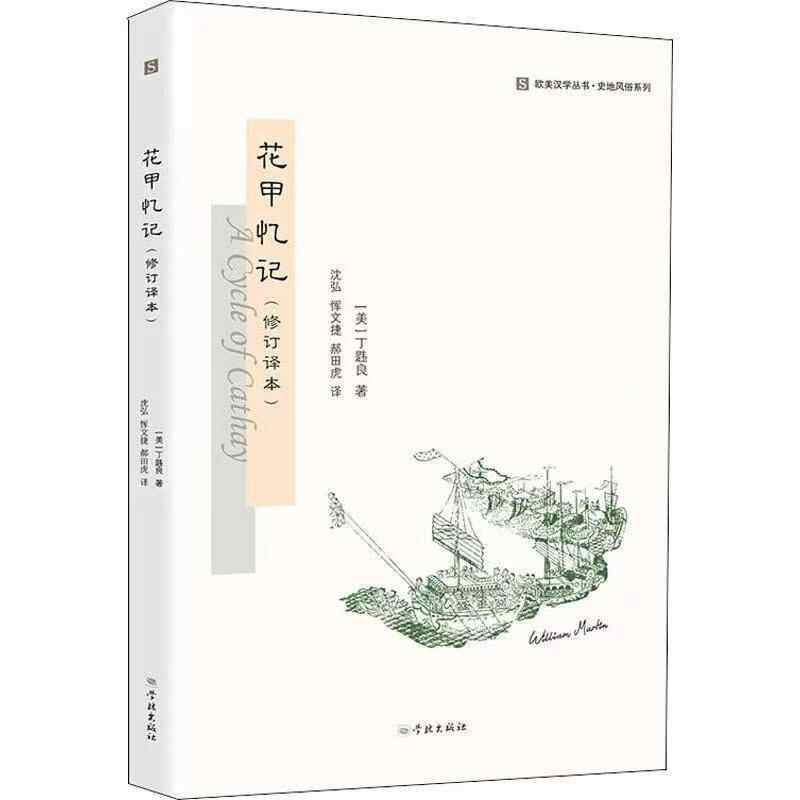
“查咸丰十年(1860)冬间,臣等于通筹善后章程内,以外国交涉事件,必先识其性情,请饬广东上海各督抚等,分派通解外国语言文字之人,携带各国书籍来京,选八旗中资质聪慧,俾资学习。而所请委派教习,广东则称无人可派;上海虽有其人,但艺不甚精。”
这是1861年10月恭亲王与其他总理衙门大臣们呈递皇帝的一份奏折选段,通过这段奏折,我们可以看出,鸦片战争以后,与清朝与各国交流的事件增多,朝廷要求广东、上海等地派出懂外语的人来北京,但广东称“无人可派”。
在这种情况下,清朝设立了培养外语人才的同文馆。对此,美国历史学家、国际汉学泰斗费正清编撰的《剑桥中国晚清史》也有阐述:
1861年总理衙门成立以后,对外交人员和翻译人员的培养就予以关注了。直到1862年才付诸实施,这一年在北京设立了同文馆。这个学堂是恭亲王和文祥1861年联名奏准成立的,他们在奏折中还建议挑选年轻、聪明的满族子弟学习外语。
在北京的同文馆设立后,在地方上,李鸿章也有类似主张。在两位著名改革派郭嵩焘和冯桂芬的帮助下,1863年巡抚李鸿章在上海设立广方言馆。1864年在广州和1866年在福州成立了同样的学府。
清朝设立的机构为什么叫“同文”呢?美国加州大学荣誉教授徐中约(Immanuel C.Y.Hsū)所著《中国的奋斗:1600—2000》中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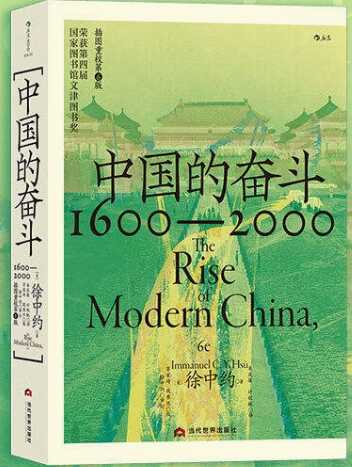
同文馆于1862年经恭亲王提议在北京开办,外国人则称其为翻译学院或外语学院。它原初被设计为一所联合教习西文和华文的学校,故有了“同文馆”之名。
可见,这个同文馆在外国人看来,就是清朝的“外语学院”。该书中也强调,该馆的创设是为了回应英、法《天津条约》中关于规定英语和法语文本为条约唯一正本的条款,清朝因此需要训练精干的语言专家,以便摆脱对洋人翻译和半瓶子醋的广东通事的依赖,那些广东通事只能说“洋泾浜”英语。
同文馆的运作
日本著名历史学家、汉学家滨下武志在《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清末海关财政与通商口岸市场圈》中说,清朝海关的主要作用在当初只限于维持对外贸易秩序,基于一定的税率以征收外国船税等。

但是,随着形势的发展,因为海关处于中国与外国交涉的接触面上,同时具有作为东西方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交流的制度性媒介这一地位,所以又具备了以下功能:同文馆的教育、翻译事业。
美国著名汉学家费正清等编撰的《赫德日记(1854-1863)—-步入中国清廷仕途》中也说,以恭亲王为首的总理衙门的重要职责范围开始得到扩大,不仅包括处理对外关系的官方事务和管理海关的任务,而且包括管理中国和西方合办的新式事业,诸如同文馆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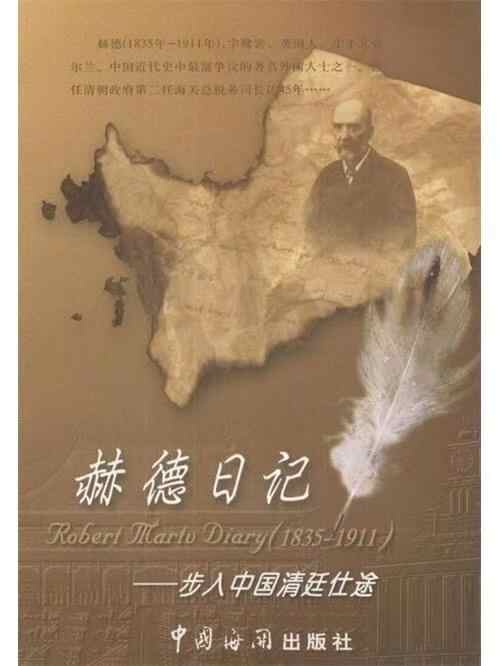
正如上述日本和美国学者所言,清朝北京的同文馆,归总理衙门下的总税务司管辖,而广州的同文馆,则是归粤海关管辖。
至于同文馆为什么归海关机构管辖?除了其有对外的作用外,更重要的原因是:海关的关税收入,为同文馆提供了经费,对此,《剑桥中国晚清史》中强调,大清国的海关基金提供了一些新办事业,如同文馆、赴美留学使团的经费。
同文馆都设置了什么课程呢?1877-1907年曾在清朝中国海关工作的美国人马士在《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一书中有介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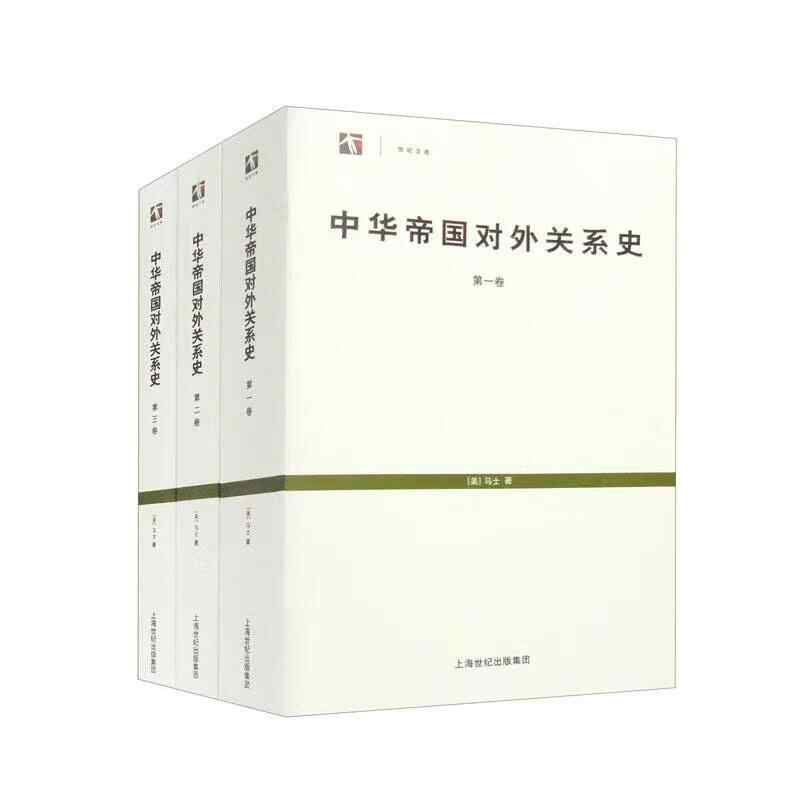
广东所办的同文馆、水陆师学堂、鱼雷学堂、电报学堂等洋务学堂,从办学方针、学制、课程设置、培养目标及教学环节都是参照西方先进国家同类学堂而创办的。
该书还介绍,在教学内容方面,同文馆设置了自然科学和各种技术学科的课程,如数学、化学、电学、植物、制造、矿学、测量、机轮、天文、海道、驾驶等,还有外语、国际法皆引入课堂。这一切,既为西方先进的自然科学和技术学科在广东的传播起了一定积极的作用,也在广东近代化的基础教育、实业教育、军事教育开了先河。这些学堂培养了一批外文、近代军事及电报、鱼雷等技术的人才。
关于同文馆的课程设计,《剑桥中国晚清史》则有更详细的介绍:设有英、法、俄、德文课程。这些语言学堂都逐渐成了西学中心。到1867年,同文馆的课程里开设天文学和数学;到1879年,又增设了物理、化学、生理学和国际法课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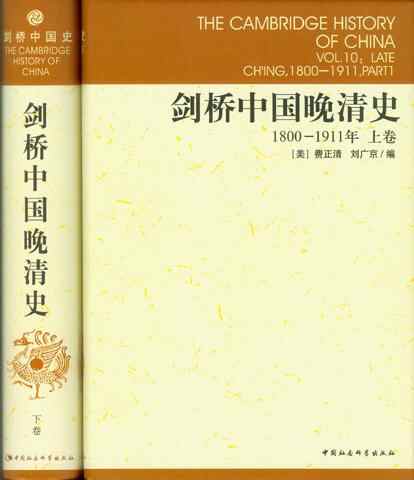
《花甲忆记(修订译本)》一书中,还详细介绍了同文馆的学生:学生都是官费生,其名额限于120人。他们又可以分为两种:一种从外语开始学习,另一种从格致学开始学起。
前者从北京的旗人中招收,往往来学习时连本国的文字也所知甚少。后者包括汉人和旗人,他们的文学水准必须要达到能通过科举考试的程度。在他们中间,获得秀才、举人和进士这三种学位的人都有。许多人在进馆之前只获得过最低的秀才,但入馆后一直学到最高的进士。
翻译书籍
同文馆除了正常的教学外,还有翻译外国书籍的职能。对此,日本著名中国经济史学家滨下武志教授在《近代中国的国际契机——朝贡贸易体系与近代亚洲经济圈》一书中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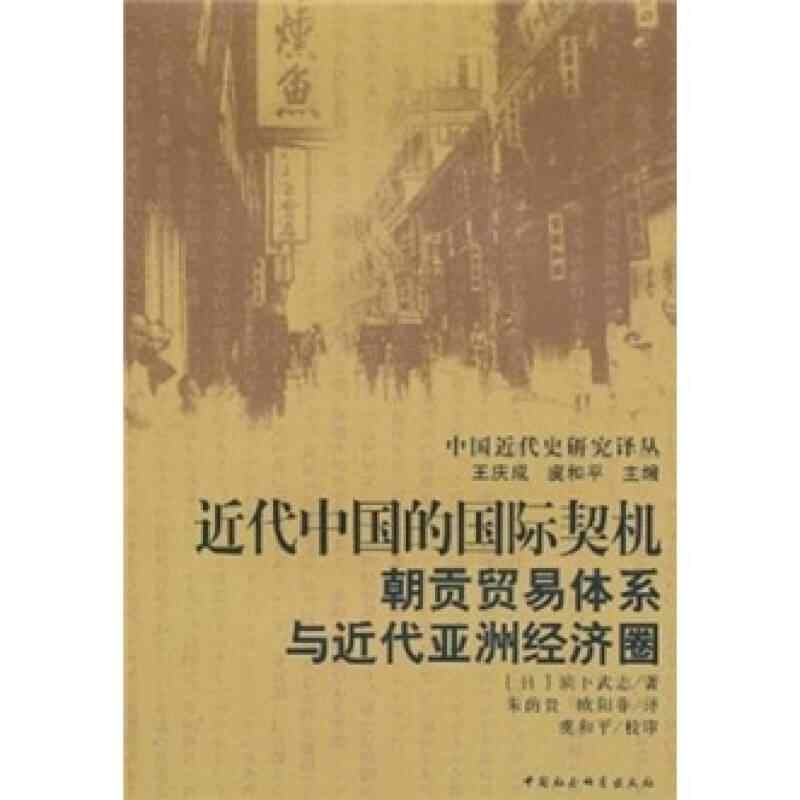
1884年5月,在伦敦举办的国际健康保险展览会上,中国政府令海关总税务司罗伯特·赫德组织参展,并通过海关从全国各地搜集展品。在该展览会上,中国的展品就包括了“同文馆翻译的中国书籍”
当然,对同文馆来说,更为重要的工作则是将一些外国书籍翻译成中文。对此,美国历史学博士皇甫峥峥在《远西旅人—晚清外交与信息秩序》提到:

两个全新的机构—总理衙门和同文馆将清政府与外国外交官及外国顾问联系了起来。应总理衙门的要求,同文馆的学生和外国教习翻译了有关国际法和外交手册的书籍,并从1870年代初开始,将翻译范围扩大至数学、科学、世界地理和历史。
《剑桥中国晚清史》也说,同文馆的出版物仍是很可观的。再加上西方传教士私人的翻译作品,数量就大大增加了。所有这些译著成为传播西学的重要桥梁。
同文馆翻译的外国书籍,对清朝时期的中国人学习西方知识发挥了重要作用。比如,美国学者、哥伦比亚大学国际全球史博士刘仁威在《茶业战争:中国与印度的一段资本主义史》一书中讲了一个案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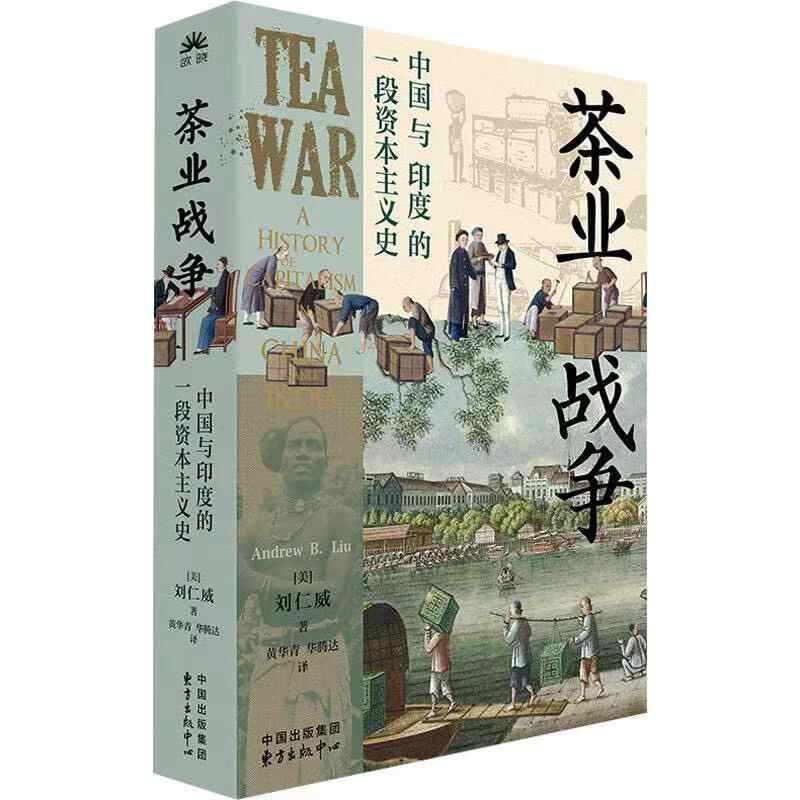
清末维新派官员陈炽,与广东学者郑观应的关系密切,他也是中国最早接触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思想家之一。
在清朝,最早被广泛阅读的著作是同文馆于1880年翻译的亨利·法思德的《政治经济学提要》(1874年版)。陈炽将这份手稿的理念融入自己的著作中,并于1895—1896年间出版《续富国策》。
旧址位于广州市越秀区朝天小学校内的“同文馆”,可以说是广州最早的外语学校,为广东培养了不少外语专业人才,在广东近代教育史上占有一席之地。
名家简介:

董兴宝,山东潍坊人,国家一级注册建造师,现为广东省作家协会会员、山东省作家协会会员。
-
【名家说岭南·卢建 丘树宏】晚清中葡关于小横琴岛舵尾山问题的交涉纪实及风波中的两广总督张之洞——横琴文史与名人故事(17)
2025-05-08 23:32:34 -
【名家说岭南·江冰主持】临水照花、相映成趣——读江冰“江南六记”
2025-05-08 20:56:45 -
【名家说岭南·丘树宏主持】《中山是座山》唱响一座城——“双百年”孙中山文化专题(34)
2025-05-07 17:18:17 -
立夏到,来岭南吃点“苦”!郭杰带你了解杜阮凉瓜
2025-05-05 07:54: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