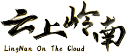

11月9日-10日,2024花地文学榜年度盛典先后在广州、深圳举行。杨知寒《黄昏后》(中信出版集团2023年7月)获评年度新锐文学,特发表其致敬辞、感言、专访——
【致敬辞】
来自寒冷的东北,“90后”青年作家杨知寒的笔尖冷峻且犀利。她在短篇小说集《黄昏后》里,一如既往地抛弃小说写作中常见的婉转,剥去生活的糖衣,留下核心位置的苦处。
从被忽视的家庭成员、日渐落寞的商场小贩,到不被认同的群体、寻求家庭温暖的白发老人……她书写那些被大浪潮吞没的小人物,并将他们的痛苦与沉默放大。但在严峻冷酷的外壳下,她又总是暗含温情与柔软,就像在严寒冬日默默升起一轮太阳,远远地,给人以慰藉。

【感言】
在每一天过去之后,重新出发
杨知寒
得奖是对过去的一次确认,我很感激,但未来的一切都还是未知。因此我能做的只有保持努力,在每一天过去之后,重新出发。
其实我小的时候在佛山生活过几个寒假,当时跟着爷爷奶奶来过冬,我记得印象非常深,这里到处都是花,有东北秋天以后就看不到的绿色,尤其是我的家乡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非常北边的一个地方。
佛山过年的时候到处都是花,还有花市,空气里还飘着一种焚香一样的气味,这些对我来说都是陌生的。当时就觉得怎么这么热闹,跟我们那里的热闹完全是两种。这里好像感觉不到寒冷和萧瑟,这里的人一年四季是否都是这么无忧无虑。
另外,粤菜还特别合我个人的口味。很多东北人都是非常喜欢粤菜的,我尤其喜欢吃狮头鹅、鱼生、生腌。几乎每次来广州,我感觉我一天得吃四顿,即便已经吃得非常撑了,仍然想再填一点,生怕回去之后吃不到这种原汁原味的感觉。
因此,这次非常感谢花地文学榜对我的关注和支持,让我可以再次来到广州。得奖是一种鼓励,也是一种督促。非常朴素的心愿,就是希望花地文学榜越办越好,以后能够组织更多、更好的文学活动,当然现在已经很好了,让更多热爱文学的人参与其中。
(文字整理:记者 文艺)

【访谈】
1、与笔下的人物“感同身受”
羊城晚报:首先祝贺你成为2024花地文学榜“年度新锐文学”得主。你近几年收获的关注很多,还记得第一次获奖,或者感受到作品被更多人看见的经历吗?
杨知寒:第一次获奖应该是2021年人民文学新人奖的时候,感觉到好像受到了一点认可。因为之前还保持一个写写也不一定能发表的状态。得到那个奖之后,的确给了我一些信心。再到后来的宝珀理想国文学奖。其实我不太知道自己在外界眼里是什么状态,或程度。因为我的生活环境相对封闭,我愿意保持这种封闭,安安静静地写东西。
羊城晚报:身处这种封闭的状态中,你似乎不是特别在意与读者的联结?
杨知寒:不,不。我很愿意和读者建立联系,我也非常看重读者的评价。但是我不想让自己过多地去关注这些事情,比如让我开设个人社交账号,更多地宣传我自己,而不是跟小说创作本身相关的东西,我觉得这些会对我有点干扰。
羊城晚报:读完《黄昏后》里的10个故事,让人感觉虽然内容一如既往的苦涩,但是你在叙事中又夹带着一丝温情和柔软。这跟以前的作品不太一样。
杨知寒:这10个故事写作的时期和心理都不一样,但是很神奇的是,自从起了“黄昏后”这个书名以后,这本书好像有了一种相对温和的气质。就像黄昏时分的阳光一样。
其实,它跟之前写《一团坚冰》等其他小说一样,就是写平常生活里大家都会经历的一些情感上的细腻时刻,一些难解的情绪。未必是多动荡、复杂的故事,但我就喜欢关注这种生活里的情绪瞬间。
羊城晚报:怎么才能精准地捕捉到如此细腻的东西,写作起来想必不是那么容易?
杨知寒:我跟书中人物的年龄、性别、身份、经历完全不一样,我的办法就是感同身受。有的时候“身受”了才能“感同”,所以尽量把自己想象成书中人物的样子和状态。虽然我们有很多的不同,但是我们的本质是一样的,都是人,吃糖会笑、摔跤会哭的人。

羊城晚报:现在再回头看,你觉得《黄昏后》中哪一篇的写作最为耗费心血?
杨知寒:应该是《美味佳药》。它是一次比较急的约稿,对方要求能反映一点社会问题。当时就想到了亲戚家的孩子,一个比我小几岁的弟弟。他性格很孤僻,不招人喜欢,但是他身上经历的那些东西,我们可能因为没经历过,所以“站着说话不腰疼”。于是我想试试去写他的家庭,他家有一些细节让我觉得很好玩,比如说他们吃饭之前总会像做祷告似的,感谢这桌饭,感谢“美味佳药”。
羊城晚报:读“美味佳药”是因为有口音吗?
杨知寒:不是,他们家不认识“美味佳肴”的正确读音,所以我每次听都觉得挺好玩儿的。
羊城晚报:以《美味佳药》为例,在小说创作中真实与虚构的部分各占多少,你又是怎么处理它们之间的关系呢?
杨知寒:五五开吧。其实还是去找你跟这个人物的内在联系,如果你是他的话,在那种处境下有没有另外一种行为模式。但这种行为模式必须是合理的,必须建立在你对这个人物性格充分了解之后,他可能会做的,但现实中可能因为种种原因他没有去做。也希望故事可读性强一点,所以就设计了一个“美味佳肴”的故事。

2、寄希望于文字上再做得好一点
羊城晚报:“杨知寒”这个名字跟家乡东北漫长的冬季有关吗,它应该不是本名?
杨知寒:是我自己起的。应该是大一或大二的时候。我也很想编一个好听的由来故事,但其实啥都没有,名字是突然想到的,脑子里没有任何思考。
最开始写网络小说的时候,也不想用本名,觉得用本名写太傻了。再者本名“艾琳”它像外文翻译过来的名字,很多外国小说的女主角会叫“艾琳”。所以我一直觉得这个名字跟“杨杰克”“杨汤姆”没什么区别(笑)。
不过拥有两个名字挺好的一个地方就是,朋友或者工作上的人就叫“知寒”,如果有人叫我“艾琳”,那一定是我非常亲近的人。
羊城晚报:可能跟你犀利的写作风格、寒冷的家乡,甚至是名字有关,很多人认为你的性格也是冷峻的。
杨知寒:其实不是这样,还会有很多的“谎言”在里面,这种“谎言”不是非要去骗谁,而是生活本就如此复杂,人就是有很多面。我觉得自己不是一个冷峻的人,我的情绪也经常失控,只不过我不是那种大吵大叫,歇斯底里的。我还算比较情绪化,内心非常敏感。但是这些时刻通常都是在亲近的人面前,以及独处的时候,才会放心地把它表露出来。
羊城晚报:对于这样的误解,你会觉得困惑吗?
杨知寒:我当然会感到困惑,但是这个事情解决不了。因为你又是一个相对封闭的状态,怎么让别人去认识你和了解你呢。如果不能认识和了解的话,误会就会存在,这是自己选择的结果。我只能寄希望于文字上再做得好一点,其他东西没办法的。
羊城晚报:近年来,涌现出一批深受读者喜爱的东北青年作家,他们又被文艺批评家称为“新东北作家群”。你也常常被认为是该群体的接力书写者,如何看待这种评价?
杨知寒:我觉得我就是一根钉子,钉子被钉到墙上,你问钉子有啥感觉,我都不能说讨厌这件事,或者多赞同这件事,就没什么感觉。
可能他们觉得这样打包处理,会不会在认识上比较方便一点?我对这些不是太了解,这种偏理论的东西我都不是太懂,也很少看。
羊城晚报:那你还是更多地专注在个体上。
杨知寒:因为我心思很敏感,我怕激起我心里的波澜,怕所有的东西会干扰到我好不容易得到的平静。
羊城晚报:那换个问题。现在越来越多的人书写东北、关注东北,从文学到影视,再到当下火热的文旅。你怎么看呢?
杨知寒:作为东北人,我自然会觉得很开心。虽然之前东北也不会被人忽视掉,以赵本山老师为代表的喜剧演员为东北带来很高的关注度。现在大家从文学的角度再去关注东北,对我来说是件很高兴的事情。
但是我想说,大家如果真的很喜欢东北的话,还是应该自己过来看一看、走一走。东北的特殊性在于它由三个省和蒙东地区组成,面积太大了。三个省虽然气息相通,但各有各的特色和不同。用“东北”这两个字,你难免会笼统地去看它,因此会留下一些刻板印象。

3、文学只是享受生活的一种方式
羊城晚报:“卷”是当下社会的常态,忙碌的年轻人自我调侃为“牛马”。而对你而言,创作就是你的工作,你又怎么看待它与生活的关系?
杨知寒:我平时不太考虑文学有什么意义或者对我有多重大,但是我非常喜欢它,应该是我最喜欢做的一件事情,这个毋庸置疑。
但是我不会把它作为我人生里唯一存在的东西,我还有其他很多途径享受我的生活,文学是我享受生活种种方式中最重要的一种。它也会让我觉得闹心或者痛苦,但是更多时候它恰恰是提供了缓解。因为当你在写别人闹心事的时候,你的闹心事就少很多,后面这句是玩笑话(笑)。
羊城晚报:如果遇到写不出的时候,这还会是一种享受吗?
杨知寒:其实我感到我一直都处在瓶颈期,很少有写得非常顺畅的时候,如果真有这种时候反而会觉得不太真实,我会控制自己的节奏再等一等。所以我觉得有瓶颈不是一件多可怕的事情。一件事情做不下去的时候未必是这件事做不成,是你的心理在当下不适合做成它,你可以去找别的一点事情做。
羊城晚报:写作是一个不断“输出”的过程,确实比较耗费心力。平常怎么给自己充电“输入”呢?
杨知寒:看书、看电影、打游戏……和人打交道也是很重要的。我其实并不排斥社交,我还挺喜欢社交。但我喜欢的社交不是那种无用社交,好像即便身处人群,但是你还是一个人,挺无聊的。还不如跟几个比较聊得来的朋友度过一段时间,那段时间你是完全身心放松的。
羊城晚报:你大学毕业后一直保持自由写作的状态,很好奇你的朋友都由哪些人组成呢?
杨知寒:可想而知,肯定是一些以前一起上学的朋友,但是这几年更多的是写作的朋友,都是好玩的人。
羊城晚报:你们坐在一起聊什么呢,聊文学吗?
杨知寒:谁聊文学,聊文学直接让他出去(笑)。
羊城晚报:最后,你在《黄昏后》的短篇《百花杀》里写了这样一句话:“三十已到,过了这关,像过了人生所有关,从没人告诉过她,一辈子居然是这样。”你今年也刚好三十岁,会觉得“过了人生所有关”吗,跟过去比有什么不同?
杨知寒:比以前感觉好多了。尤其是从20岁出头到25岁,再到30岁,这几年我觉得性格变化是比较大的。看问题不会像之前那么尖锐,没有那么容易动气、动情。
当然这种尖锐的东西在写作里会有好的表现,比如会很容易感染到读者。我现在的情绪表达在真诚的基础上会稍稍节制一点。真诚是一切的基础,这个是不会变的。30岁以后我真的觉得好多了,而且我现在非常期待40岁。
文字访谈|记者 文艺
图、视频拍摄|记者 宋金峪 曾育文 周巍 梁喻 实习记者 杨江
视频剪辑、包装|记者 麦宇恒 余梓涛
总策划:任天阳
总统筹:林海利
总执行:胡泉 陈桥生
统筹:邓琼 吴小攀
执行统筹:朱绍杰 孙磊
-
【名家·李敬一】汉赋:洋洋大观一代之文学
2024-11-22 09:16:00 -
【名家·张春晓 杨润莲】广府文化传承中的木鱼书
2024-11-22 09:15:59 -
【名家·曹林】曹林:培养“迟钝感”,少看畅销书
2024-11-22 10:00:00 -
【名家·张翎】张翎:现实是虚构的基础,虚构就是“构而不虚”
2024-11-20 10:19:0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