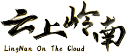

□ 李敬一
人言“诗词歌赋”为才情,今人少有谈“赋”才者;人谓“诗词曲赋”属四体,今人少有诵“赋”篇者;人论汉赋乃“一代之文学”,今人少有识汉代大赋者。王国维《宋元戏曲史·序》云:“楚之骚,汉之赋,六代之骈语,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文学。”汉赋,乃人人关切却相对陌生的一种文学样式,它虽“冷门”,却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块瑰宝。
“赋”的本义是什么?南北朝时刘勰《文心雕龙·诠赋》说:“赋者,铺也。铺采摛文,体物写志也。”宋代朱熹《诗集传》说:“赋者,敷陈其事而直言之者也。”可见,“赋”,最初只是文学创作中的一种写作方法,偏重铺张叙述。
“汉赋”则是西汉时,文人袭用“楚辞”的体制和夸饰铺陈的表现手法,来叙事写物,而仿效荀子以“赋”名篇(荀子有《礼赋》《知赋》《云赋》《蚕赋》《箴赋》),创造的一种散文和韵文结合的“半诗半文”的文学体裁。它不能算是诗歌,但却是从诗歌衍变而来,是“古诗之流”。它受到楚辞表现手法上的很大影响:篇幅很长,洋洋大观;夸饰铺陈,达到无以复加的程度;多采用人物对话或主客问答的方式从不同角度、不同层次展开对内容的铺述;好用艰深的辞句和生僻的文字;喜用比兴手法来展现文章内容;依然具有“书楚语、作楚声、纪楚地、名楚物”的地方特色;以“兮”字表节奏,等等。因为它继承了楚辞的一些表现手法,所以人们也称其为汉代“辞赋”。
汉赋在当时文坛占主导地位。汉武帝以来至东汉中期的大赋,在形式上虽然受“楚辞”全面影响,但在内容上却没有“楚辞”那种强烈的以现实主义为基础的抒情性和批判性,很少直接反映当时的普通群众生活,也不注重揭示深层的社会矛盾,它只是以夸张的手法,板滞的形式,描写宫苑的富丽,都市的繁华,物产的丰饶,统治者成仙渴望、田猎乐事,对统治者极尽歌功颂德之能事。其中有一点点讽谕的意味,也不过是“讽一而劝百”,比如:写统治者车骑之乐,则捎带说一声“乐万乘之侈,恐百姓被其尤”。形式上,往往采用最华丽的词藻来弥补内容的不足;以最生僻的文字来夸示自己的才学。可以看出,汉赋是太平盛世政治伦理、社会风气下文学重政治、重说教、重形式的产物。
汉赋的兴盛,大体是因为当时太平盛世,社会安定,经济繁荣,疆域扩大,统治者需要有人为其歌功颂德,需要精神上的奢侈品和点缀品。同时,又因为汉代统治者出身楚地,提倡楚辞,喜欢楚文化那种神秘、诡异、夸张的特色。包括秦末汉初的统治者,其作品如项羽的《垓下歌》(“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刘邦的《大风歌》(“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都是半诗半文的“赋”的形式,至于刘、项之后的汉代治国者,更是如此。可以说,汉代之后,中国文学“楚”化了!此外,汉代有非常宽松的献赋、考赋制度,赋写得好可以得宠、做官,故文人争相作赋,形成风气,不足为奇。当然,《诗经》之后,四言诗已经衰落,五、七言诗正在民间酝酿而没有进入文人的创作领域,因而“楚辞”这种铺张扬厉的表现形式和荀子“赋”体得到发展,写辞作赋成为文人的“时尚”,这种文学自身发展的规律也推动了汉赋发展进程。而且汉代自武帝之后,政治思想上“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而汉赋歌颂与讽谕的主旨又恰恰符合统治者宗经原道的政治文化需要。

当然,汉赋发展成洋洋大观的样式并非一日之功,自汉高祖至汉景帝六七十年间,赋家主要模拟楚辞,多用“兮”字,内容上抒发政见,论说哲理,感慨身世,半诗半文,形成独特体制,尚未流入形式主义,代表作家有贾谊和枚乘。
贾谊的代表作有《吊屈原赋》和《鵩鸟赋》,其中《鵩鸟赋》是贾谊被贬至长沙之后见鵩鸟(猫头鹰)入其室而作。当地风俗,鵩鸟至于人家,极为不祥,主人必死。贾谊以此为由,论生死祸福、万物变化,说理特点突出:“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忧喜聚门兮,吉凶同域。彼吴强大兮,夫差以败;越栖会稽兮,勾践霸世。斯游遂成兮,卒被五刑;傅说胥靡兮,乃相武丁。夫祸之与福兮,何异纠纆;命不可说兮,孰知其极!”《吊屈原赋》则是贾谊贬赴长沙、途经汨罗江畔,有感于与屈原相同的身世,悲愤而作,抒情色彩鲜明:“恭承嘉惠兮俟罪长沙;侧闻屈原兮自沉汩罗。造托湘流兮敬吊先生:遭世罔极兮乃殒厥身。呜呼哀哉!时逢不祥。鸾凤伏窜兮鸱枭翱翔。阘茸尊显兮谗谀得志;贤圣逆曳兮方正倒植。……”
枚乘代表作是《七发》。《七发》写“楚太子”有疾,不理政事,精神恹恹,卧床不起,“吴客”前往拜访,用七段话向“楚太子”进说,终于打动对方,令其沉疴顿癒,振奋起来:一发之以琴音之赏,楚太子“病未能”;二发之以滋味之腴,楚太子“病未能”;三发之以车马之快,楚太子依然“病未能”;四发之以游观声伎,楚太子还是“病未能”;五发之以畋猎,楚太子“有起色矣”;六发之以观涛,楚太子却又“病未能也”;直至七发以圣人辩士之“要言妙道”,太子才“据几而起”,“涊然汗出,霍然病已”。文章说明,贪图享乐,奢侈腐化,乃百病根源,于治病无效,对健康无益;而读书学习,“要言妙道”,才是疗病良方,使人向上。枚乘的赋标志着汉赋由“诗”向“文”的转变:其作辞藻华美,形式夸张,“腴辞云构,夸丽风骇”(《文心雕龙·杂文篇》)。而且,词汇丰富,描写细腻,如六发写波涛:“疾雷闻百里,江水逆流,海水上潮,山出内云,日夜不止。……波涌而云乱,扰扰焉如三军之腾装;其旁作而奔起也,飘飘焉如轻车之勒兵”,形象鲜明,有声有色。《七发》已经离开楚辞的抒情性和贾谊《鵩鸟赋》的说理性,主要叙事写物,于叙事中说理,并且用反复问答的形式,演成一段故事,成为后来赋作的基本模式。
武、宣、元、成时期,亦即西汉中期,则是汉赋的全盛时期。《汉书·艺文志》所载汉赋九百余篇,作者六十余人,其中十分之九是这时候的作品。代表作家是司马相如。司马相如的赋共二十九篇,大都失传,流传下来的代表作品仅有:《子虚赋》《上林赋》《大人赋》《长门赋》《美人赋》《哀二世赋》诸篇。相如赋最突出的特点是:写景状物尽量铺叙夸张以至于失去真实性,无论什么珍禽怪兽,异草奇花,只要头脑中想到的,一齐排列出来;任何写景,都是上面怎样,下面怎样,左边怎样,右边怎样,东边怎样,西边怎样,南边怎样,北边怎样,中间怎样,几乎成为一种板滞的模式。如《子虚赋》(节录):
云梦者,方九百里,其中有山焉:其山则盘纡岪郁,隆崇峍崒;岑崟参差,日月蔽亏。交错纠纷,上干青云;罢池陂陁,下属江河。其土则丹青赭垩,雌黄白坿,锡碧金银;众色炫耀,照烂龙鳞。其石则赤玉玫瑰,琳瑉昆吾;瑊玏玄厉,碝石碔砆。其东则有蕙圃:蘅兰芷若,芎藭菖蒲,江离蘪芜,诸柘巴苴。其南则有平原广泽:登降陁靡,案衍坛曼;缘以大江,限以巫山。其高燥则生葴菥苞荔,薛莎青薠;其埤湿则生藏莨蒹葭,东蘠彫胡,莲藕觚卢,菴闾轩于。众物居之,不可胜图。其西则有涌泉清池,激水推移:外发芙蓉菱华,内隐钜石白沙;其中则有神龟蛟鼍,瑇瑁鼈黿。其北则有阴林:其树楩栴豫章,桂椒木兰,檗离朱杨,樝梨梬栗,橘柚芬芳;其上则有鵷鶵孔鸾,腾远射干;其下则有白虎玄豹,蟃蜒貙犴。
尽管如此,但相如赋能从多视角、多中心来观察和描写事物,却也是文学表现手法的跨越性进步。同时它讲究声音美,讲究排列美,重写景、重铺排,词汇丰富,洋洋大观,感染力强,也增强了文学作品的语言文字表现力和艺术鉴赏价值。
相如赋是汉赋的最高代表,后代赋家以模仿他的大赋为能事,从题材到篇幅,从语言到风格,均不出其范围,西汉末年至东汉中叶这类作家的代表便是扬雄和班固。扬雄的代表作品《甘泉赋》《羽猎赋》《长杨赋》《河东赋》,模拟司马相如的《子虚赋》《上林赋》。班固的代表作品《两都赋》(《西都赋》《东都赋》),也是模仿《子虚赋》《上林赋》。但是,扬雄、班固虽以模仿司马相如为能事,却因为他们才学宏富,模拟起来别具一格,故有“扬马”“班马”之并称,赋史亦留其美名。
东汉中期至东汉末年,社会动荡,民生凋敝,文人落魄,英雄气短,一事一物,时有所感,形诸文字,则见小赋盛行,赋又回归了早期的抒情特色。代表作家有张衡、赵壹、蔡邕、祢衡等人。
张衡的代表作《两京赋》(《西京赋》《东京赋》),“精思傅会,十年乃成”,依然模仿《子虚赋》《上林赋》并试图以此压过班固《两都赋》,但影响最大的还是他的《思玄赋》《归田赋》《髑髅赋》等小赋。赵壹的代表作为《刺世疾邪赋》,蔡邕的代表作为《述行赋》,祢衡的代表作为《鹦鹉赋》,此赋写于江夏郡长江中的一个小洲,此洲遂名鹦鹉洲,在今湖北武汉市内,洲名影响颇大,得益于此赋。
总之,汉赋是中国历史上国力强盛、疆域宽广、经济繁荣、社会安定的时代印记。汉赋的产生,印证了“乱世有乱世文学,盛世有盛世文学”的规律,它热爱生活,崇尚自然,维护统一,善唱赞歌,也为后世文学创作提供了许多启示和认识。汉赋的文学价值还在于它扩大了文学表现力,丰富了文学艺术手段,进一步展示了文学的价值和美感。汉赋之前(包括楚辞之前),文学创作手段主要是简单的“赋、比、兴”;汉赋之后,文学家们知道什么叫描写,什么叫夸张,什么叫铺排,什么叫篇章……“赋体”作为一种有特色的文学样式,在中国文学史上别具一格:它比诗、词宏大,气派,却比诗、词创作更显自由;它比普通散文华丽、多彩,却比散文更为精悍。汉代之后,虽然“诗词曲赋”四体并称,但“赋”实际上统兼统含:它是诗,是文,是短语,是长吟;它行文或咏,或叹,或叙,或议,均挥洒自如,变幻莫测,自是一道美丽的风景线。它是中国文学史上最大气、最美丽、最神秘的一种诗文结合体,也是今人最易掌握的一种文学形式,它大体要求是:铺张描写,层次清晰;骈四俪六,排比对偶;词语精炼,节奏分明;抑扬顿挫,韵律和谐;中心突出,能放能收。所以,我们仍需了解它,诵读它,学习它,掌握它,这也是笔者撰写此文之目的。
(作者是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主讲人)
-
【名家·张春晓 杨润莲】广府文化传承中的木鱼书
2024-11-22 09:15:59 -
【名家·张翎】张翎:现实是虚构的基础,虚构就是“构而不虚”
2024-11-20 10:19:04 -
【名家·陈平原】陈平原:我很庆幸自己的学问和生活不止一个支点
2024-11-20 10:04:52 -
【名家·陈永正】陈永正:弘扬岭南诗教,赓续中大文脉
2024-11-20 09:46:4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