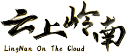

“日啖樱桃三百颗,不辞长做醍醐人。”
在岭南的悠悠岁月里,苏轼留下了“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的千古名句,那是他对这片土地发自肺腑的热爱。
而在遥远的陕西渭南澄城县,有一个名为醍醐村的地方,虽与岭南相隔千里,却在我的心中,与苏轼笔下的岭南产生了奇妙的共鸣。
我的许多北京同事和外地朋友,因我的文字结识了醍醐村。在他们的想象中,这里仿若世外桃源,风景秀丽,民风淳朴,物产丰富,一年中有三季都弥漫着瓜果的香气。尤其是那樱桃,颗颗饱满,甜润多汁,对我的吸引,恰似荔枝对苏轼的诱惑。
他们羡慕我能在这驻村三年,享受着这般宁静悠然的田园生活。

但本地的同事却对此嗤之以鼻,在他们眼中,醍醐村不过是个再普通不过的村落。这里村庄破旧,经济落后,虽说盛产各类水果,可比起周边地区,却都差了几分火候。樱桃比不过县北的鲜甜,花椒比不上韩城的醇厚,冬枣比不过大荔的脆爽,苹果比不过白水的香甜,柿子比不过富平的软糯,黄花菜也比不过连家城的鲜嫩,毫无出众之处。

不得不承认,他们的话有一定道理。如今的醍醐村,是个典型的空心村,只剩下老人和孩子守着这片土地。平日里,街道冷冷清清,店铺大多关门歇业,鲜有人声,连鸡鸣犬吠都变得稀少。街边,老人们或是弯腰照料着门前的小菜园,或是几人围坐,沉默地晒着太阳。偶尔,还会遇到个别村民为了些许利益,与企业发生争执。
可即便如此,我对醍醐村的喜爱却丝毫不减。在我心中,它就像一位久违的老友,初次相见,便已情根深种。

从暮春四月到深秋十一月,我最爱漫步在广袤的田野间,感受着四季的更迭,目睹着瓜果的成熟。那是一场视觉与嗅觉的盛宴,香瓜的清甜、樱桃的鲜嫩、酥梨的爽口、西瓜的沙甜、葡萄的馥郁、黄杏的酸甜、柿子的软糯、核桃的醇厚、石榴的多汁、苹果的香脆,轮番登场,令人陶醉其中。
我也喜欢穿梭在村子的大街小巷,端详着每一家店铺的招牌,那些名字或质朴、或雅致,都藏着生活的烟火气;走进村民的院子,欣赏他们独特的房屋布局和家具陈设,感受着这份质朴的生活气息;听着村民们用方言闲谝斗嘴,品味其中的妙趣;晒秋时节,与他们聊聊花椒的成色、黄花菜的行情,分享着收获的喜悦与忧愁。

哪怕周末节假日,我独自守着简陋冰冷的宿舍,无人陪伴;哪怕寒冬腊月,天地间一片萧瑟,无处可去;哪怕面对村企之间复杂的矛盾纠纷,我对这片土地的热爱,依旧炽热如初。
事实上,就算没有那令人垂涎的樱桃,我对醍醐村的爱也不会有丝毫改变。

每当捧起苏轼的《惠州一绝・食荔枝》,我都仿若穿越千年,与东坡先生心意相通。
苏轼被贬惠州时,那里还是岭南的荒蛮之地,是罪臣的流放之所。垂垂老矣的东坡先生缺衣少食、无家无友,只能暂居在郊外的寺庙。可一生颠沛流离、屡经磨难与打击的东坡,并未因此哀怨沉沦,而是坦然接受,不以己悲,入乡随俗,扎根异乡,满怀喜悦地去发现生活中点滴美好,在文字中毫不掩饰对岭南山水风物的喜爱。
别人看到的是惠州的偏远荒凉、民风鄙陋、环境恶劣,而东坡眼中的惠州,罗浮山风景独特,气候温暖,四季如春,荔枝、柑橘、龙眼、杨梅等瓜果不断,还能每日实现“风骨自是倾城姝”的荔枝自由。
对一个吃货而言,即便再也不回繁华城市,不再做朝廷命官,一辈子在此安营扎寨,也值了!
但东坡“不辞长作岭南人”,难道仅仅因为“日啖荔枝三百颗”?我相信,即便没有味美的荔枝,也会有别的事物,或山,或水,或人,或物,都能让东坡乐于斯、爱于斯!
因为无论身处何方,无论道路如何艰难险阻、荆棘丛生,超脱豪迈、乐观宽容,始终是东坡一生的追求!
惠州之于东坡是如此,黄州、儋州亦是如此。
而醍醐村,对于千载之后东坡无数仰慕者之一的我来说,同样如此!
【作者简介】
杨雪飞,女,1969年出生,文学硕士,国企干部。自幼受文学熏陶,热爱文字。著作有散文集《江南之春》《有字如是》《雪上飞鸿》。
【名家简介】

江冰,广州岭南文化研究会会长、广东省文化学会副会长、广东财经大学教授。入选中国作家协会新锐批评家、广东省十大优秀社会科学普及专家、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界最有影响力学者。出版有《岭南乡愁》《文化岭南》等十多部著作。
-
【名家说岭南·江冰】广州黄大仙祠,根系在日常,根系在民间
2025-02-04 14:51:44 -
【名家说岭南·江冰】广州春节观影:战火从未熄灭,我们需要文化自信,也需要中华好男儿
2025-02-02 12:02:26 -
【名家说岭南·江冰】广州感受年味:行花街,贴挥春,派利是,最让人温暖的就是人情味
2025-01-26 13:03:39 -
【名家说岭南·董兴宝】厘金制度——外国人笔下的岭南风土人情(57)
2025-01-25 22:35:0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