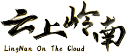
“以金属为货币,开于三千年以前。或刀形,或方形,或中穿方孔,各种不一。今铜钱因仍古形,历代不换。物价以铜钱为本位。金银虽为通货,未曾为本位。”
日本旅行者冈千仞曾在中国多个城市旅行,在明治十九年,即1886年出版的《观光纪游 观光续纪 观光游草》中的一段记载,概括性地讲述了我国自古以来使用铜钱的历史。
在许多人印象中,说起古代民间金钱交易情况,人们自然会想起清代吴敬梓的长篇小说《儒林外史》中“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 的说法,用银子交易,似乎是当时民间的主流交易方式。
但事实上并非如此,清朝的大多数时期,铜钱依然是法定的货币,民间大量的小额交易使用铜钱。
清朝时期,到过广州或研究岭南近代史的外国人,也记录了当时中国铜钱的使用情况。
唯一合法硬币
“这个帝国除了铜钱之外别无其他硬币,人们对铜钱已很熟悉,它仅用于人民的日常生活之需,除了货币兑换商用来增加其储备外,在重大的交易中从不使用铜钱。尽管这种货币的规格很低,却给每个人带来了方便,这是很聪明的做法。”
这是1829-1842年在广州美商旗昌洋行工作的美国人亨特,在其著作《广州“番鬼”录》中的一段记载。他的描述是正确的,总结是形象的,作为我国古代长期流行的货币,以“硬币”形式流通的只有“铜钱”了,而金银固然可谓是“天然货币”,但并非标准的硬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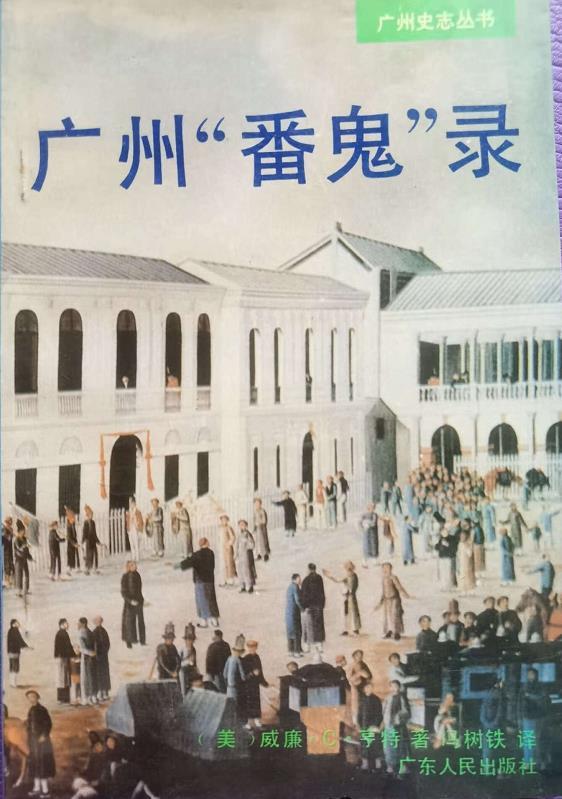
美国人亨特还观察到:当时在广州流通的铜钱,正面铸着铸钱时在位皇帝的年号,并有“通宝”两字。当然,他同时也说,如果需要更大价值的货币,则通常使用便于携带的金条或银碇。
显然,铜钱是价值比较低的货币。那么,在19世纪中期的广州,一个铜钱能买到什么呢?美国人亨特在他的另一本著作《旧中国杂记》中给出了答案:
《圆明报》在外侨中称为《广州官报》或《朝报》,是主要报道官员们的活动。这份报是用木版印刷,每张卖一两个铜钱,城里城外的街上到处都有卖。
在清朝中期的广州,铜钱在民间或市场上的使用情况又是如何呢?1752年,瑞典人彼得·奥斯贝克到达广州旅行后,在其著作《中国和东印度群岛旅行记》中提到了铜钱使用情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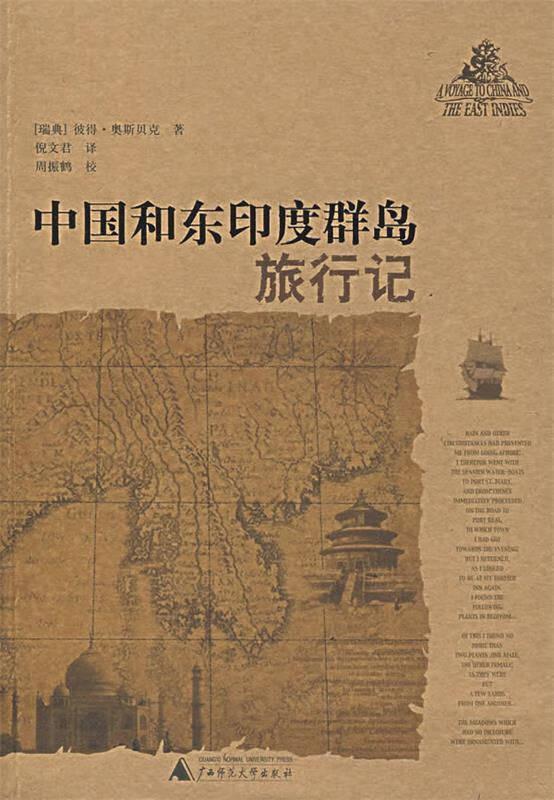
那种浅褐色的、欧洲人用来制作放置衣物的箱子的木头非常贵,我买了一个5英尺长、2英尺宽、涂漆镶铜的箱子用来放我的衣服,要100个铜钱。
该书中还说:中国人一般由裁缝挑选布料,之后一起付账:一件缎子马甲和一条缎子的马裤(夹裤)一共5两或70个铜钱。
随着广州对外贸易开展,许多大额的交易,则是使用银子。可见,当时的广州,银子和铜钱同时使用。
对此,两位美国女学者韩书瑞(SusanNaquin)和罗友枝(Evelyn Rawski)合写的著作《十八世纪中国社会》中说:
长期以来中国经济就是建立在一种双金属通货制的基础之上,日常购物用铜钱,较大的商业交易用白银。16世纪白银成为通用货币,大部分税收都以银子来计算交付,这种做法一直延续到清代。
而对于晚清时期,铜钱和银子同时使用的情况,德国《法兰克福报》记者保罗·戈德曼,受报社指派,来到了中国采访,写下了《1898年的夏日:一个德国记者的中国观察》一书,该书中有生动的描述:
在这间票务室里充满着鸦片的味道,屋内的一个角落便是员工们过夜的地方。很小的空间旁还有个洗头的盆子,在员工们身旁的桌子上还有他们的算盘,除此之外,桌子上满是成串的铜钱。中国人买票是以铜钱支付,欧洲人则以银两支付。
当然,对于日常百姓交易使用铜钱的情况,早在明朝末期来华的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也观察到了。《利玛窦中国礼记》中说,在中国很多地方,买卖较小时就使用一种小铜钱,它是官办的造币厂里铸造出来的。
美国行政法专家、1913年曾担任北洋政府宪法顾问的美国人古德诺在其著作《解析中国》中说:中国人唯一的铸币是铜钱,至今仍被普遍使用;铜钱的中央都铸有一个孔,可容一条绳子穿过,由于每个铜钱的价值都很小,因此可以看到它们常成百上千地被串在绳子上。
我们从中也可以看出,铜钱的价值虽然不大,但确是官办的铸造厂铸造的,正如《十八世纪中国社会》中说:“铜钱要铸造,而银子不用铸造。这两种货币金属的兑换率随着供应情况很容易波动,对所有百姓有直接的影响。”
既然是白银和铜钱都可以流通,必然存在两种货币的兑换,那么,这两种货币的兑换,对古代百姓的生活有什么影响?接着阐述这个重要问题。
银铜兑换比例
“因为农民是用铜钱或谷物交纳赋税,但官吏上解时用的是银两,所以实际的税率取决于需要多少铜钱或谷物折算成定额的银两数目。由于白银越来越稀少,因而它与其他货物相比就贵了起来,结果使实际的税率翻了一番或者更多,从而使小土地所有者陷于绝境。”
这是美国历史学家、国际汉学泰斗费正清编撰的《剑桥中国晚清史》中的一段话,该段话的背景是:在19世纪30年代,鸦片大量输入广东等地后,白银大量流出国外,而这种收支的不平衡迅速破坏了税收和商业。银与铜的比价变化,这几乎使所有社会集团都身受其害,唯独投机者、兑换商和高利贷者除外。

可见,铜钱与银子的兑换比例,关系到各方的利益,受损害最大的自然是普通人的农民和手工业者。
在我国历史上,铜钱与金子的兑换比例问题,日本经济学专家滨下武志在《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清末海关财政与通商口岸市场圈》书中,研究了大量中国货币、金融的权威资料,他认为:
在中国的货币流通史上,几乎没有过黄金流通的历史,基本上是白银与铜钱复本位制。其中,铜钱归中央管辖铸造,白银则由民间银炉铸成马蹄银,作为秤量货币流通。而两者的比价从1000:1(白银1两=铜钱1000文)出发,因时代的变化而又形成很大的价别。尽管中央政府并不直接管理白银的流通,但在制定征税政策时,因“地丁银”和“一条鞭法”的实行,从而在客观上确定了以白银作为收纳的主要形式。
关于铜钱与银子兑换比例的变化及带来的影响问题,还有更多外国人进行了记载。比如,1877-1907年曾在清朝中国海关工作的美国人马仕在.《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中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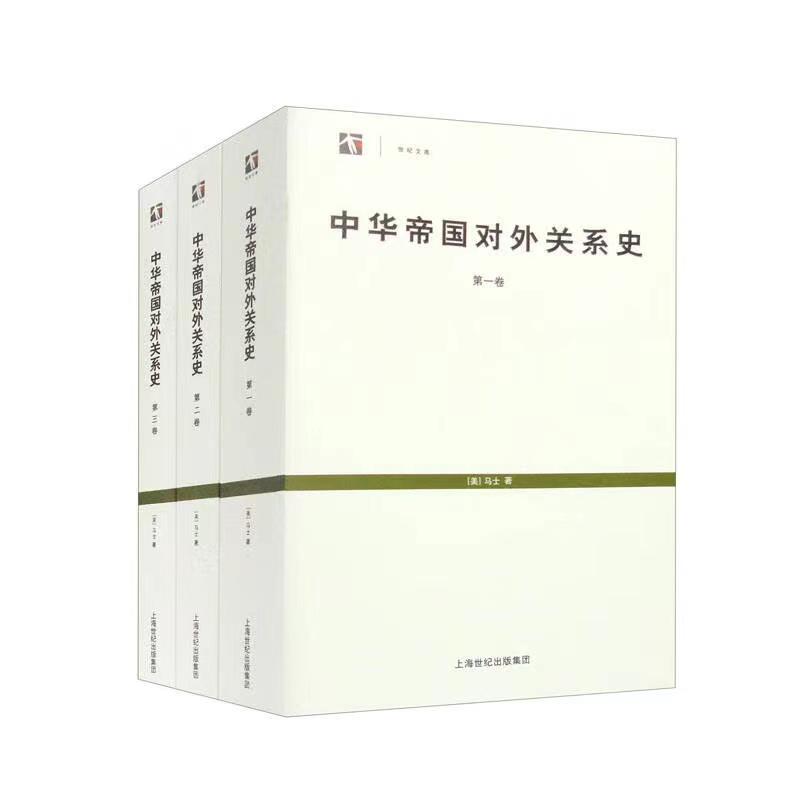
所有上奏折的人们都指出兑换银两所需铜钱数额的增加,兑换率已从一千文增到一千二三百文,而把这点作为因白银源源外流致价值上涨的证明。
可见,当时因鸦片大量输入中国,导致了白银外流,进而导致了铜钱的贬值,最终坑害了普通的百姓。马士还强调:
中国是一个在各种货币之间没有任何固定兑换率的国家,甚至在两种同样金属的货币之间也没有固定兑换率;但是所有的兑换都是受货币的本身价值和它的供求关系所影响的。
根据马士的记载,从乾隆年间的足重铜钱起到嘉庆年间,钱的分量已逐渐减低,而道光年间铜钱分量减低更甚;铜钱本身价值的损失足以使其交换价值丧失20-30%。
对于上述情况,《简明广东史》中也有记载:鸦片大量输入给中国人民造成严重的危害。由于白银大量外流引起银价飞涨。十九世纪初,1两白银只换1000文铜钱,而到1889年则可换1678文。
铜钱的海外影响
清朝早期是闭关锁国的,而清朝晚期则是非常羸弱的,那么,作为国内广泛流通的铜钱,在海外是否有影响力?答案是肯定的。
比如,《十八世纪中国社会》中说:清朝时期,中国的帆船贸易主要由来自岭南和东南沿海的商人控制,他们运瓷器、棉花、丝织品去马尼拉,以交换墨西哥银元,还向东南亚运去陶瓷、纺织品、药材和铜钱,以交换熏香、象牙、胡椒和稻米。
可以看出,当时广州大量的帆船出海,用铜钱及更多的货物,换回墨西哥的银元、稻米等。
事实上,当时的中国的铜钱,在东南亚一些国家有一定的影响力,比如,德国人贡德·弗兰克在其著作《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中说,缅甸不仅从中国进口大量的生丝、食盐、铁器和铜器、兵器和火药,而且进口布匹、绸缎、丝绒、针线、地毯、纸张、水果、茶叶以及铜钱。
小小的铜钱,在现代人看来,其价值低,似乎是不起眼的东西,但在清朝早期或中期的国际贸易中,却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名家简介】

董兴宝,山东潍坊人,国家一级注册建造师,现为广东省作家协会会员、山东省作家协会会员。在广东工作6年,曾担任广东清远市政府文化顾问(2014-2018年)。主编出版过《北江茶道》(南方日报出版社2014年出版)、《清远故事》(新华出版社2017年出版)和《中华洞河之道》(广州出版社2018年出版)等书籍。
-
【名家说岭南•徐惠萍】留美幼童:中国现代化之路最早的火种——留学文化之《容闳图传》解读(10)
2024-11-24 15:00:09 -
【名家说岭南·江冰】2024广州茶博会:花开在眼前,并非看见,而是相信
2024-11-22 17:02:33 -
莞香悠扬小雪时 国家级非遗传承人黄欧介绍莞香文化
2024-11-22 13:00:04 -
【名家说岭南•董兴宝】牙行旧事——外国人笔下的岭南风土人情(48)
2024-11-22 12:55:4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