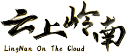
摘要
西方传播学研究是在主体预设的前提下展开的,而庄子的“吾丧我”却体现了不一样的主体性消解的逻辑,这是华夏传播研究可以为世界传播研究提供的贡献。庄子认识到,主体在世界中总有一种“无可奈何”的疏离感,与世界存在某种“间距”;由于“物”被赋予价值而被客体化,从而使得主体常常陷落其中,无法获得自由、开放与敞开。正是通过语言的反思,附着在客体上的价值被清除,主体便摆脱了客体的纠缠而实现了自由。最根本的,还是通过“心斋”“坐忘”“凝志”等方式实现“吾丧我”,即通过主体性的消解以实现主体的敞开,最终实现“物化”式的主客交融,以克服传播的沟壑。
庄子是如何通过“吾”“我”等主体人称代词的思考来处理人与世界的关系,从而获得主体趋近世界的路径的?这是一种不同于西方传播学主体支配下的逻辑,因为“在西方传播学的传统中,人都是一个核心主体,而人的存在又是通过他人或世界而得以形成的,他人或世界就成为讨论的重点;这看起来试图确立主体的地位,主体其实以不可追问的方式被隐藏了起来。”[1]无论是传播管理学派体现的主体控制世界的欲望,还是批判学派追求主体解放的取向,以及马丁·布伯的“我-你”对话关系和“我-它”主客模式,都是在主体的基础上开始发问的,即其中主体性都是一种不加追问的设定。约翰·杜翰姆·彼得斯(JohnDurhamPeters)认为“交流注定充满沟壑”[2](P377),其解决办法则是深具基督教信仰背景的关爱和宽恕,体现的也是主体的施与。很显然,彼得斯的观点在交流的障碍与解决的办法之间,存在着明显的逻辑跳跃。其原因也许在于,基于基督教信仰的兜底信念,“关爱”和“宽恕”是从主体这里直接生发出来而不是逻辑延伸出来的。
而华夏传播思想中则存在着运思上的巨大差异,常常采用的是老子的“损”、孔子的“克”、王阳明的“磨”、佛教的“斩”等等“内敛”的主体性消解逻辑,并以此获得主体趋近世界的路径。庄子的逻辑则体现在“吾丧我”(《齐物论》:35)1这一表述当中,其中就包括“心斋”“坐忘”“无己”“虚己”“忘己”“忘我”“外生”等主体性消解的功夫。他试图通过主体性的消解(“丧我”)实现主体的完全敞开,找寻到主体趋近世界的路径,以处理主体与自我、他人以及万物的关系问题,最终实现“和以天倪”“道通为一”“万物皆一”的传播圆融状态。这种超越主体运思的局限性,并将人与自我、人与人、人与物的关系皆纳入平等讨论的思路,使得传播研究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广阔视野,可以很好地回应当下社会中的心态问题、社会冲突问题和生态破坏问题。
一、可传不可受:主体的疏离与传播的焦虑
在庄子的思想深处,总是存在着“我是谁”的深深的主体疏离感,主体处在一种缺乏掌控感的自我漂浮之中。这就为庄子思考主体问题,以及主体与他人、与万物等传播问题奠定了起点。也正是这种疏离感,使得庄子能超脱于主体之外,从另外一个更加宏阔的视野来看待人、他人、人类与万物,而不再纠缠于主体的界域。这种宏阔视野的获得,也正是基于对传播的焦虑的克服,即主体疏离背景下一种“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的自修。而这种自修并不是“为我”,而是通过“吾丧我”的主体性消解来实现“以天合天”,从而达致主体与世界的趋近。
首先,自我无法掌控自身,自我与生命、身体、器官、能力以及世界之间存在着深深的疏离感,这是一种无可奈何的主体性极弱的存在状态。一个人的身体、生命、本性和子孙都是天地给予的,并不是自己所能拥有的,不在自己的掌控范围(《知北游》:595-596);人的生命最多也不过百岁,而且总是充满生老病死与忧患(《盗跖》:807)。这就使得庄子常常发出“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的感叹(《养生主》:94)。身体也没有一个主宰者,因而总是被裹挟到周围的世界当中:身体器官之间不存在支配与亲疏的关系,人的生命在奔波中消耗,总是不得不与外在的环境相对立、相适应、相磨合,由此奔忙一生而无法停止(《齐物论》:45-47)。人类的认知能力也总是受到身体所在时间、空间和语境的严重限制,因为“井"不可以语于海者,拘于虚也;夏虫不可以语于冰者,笃于时也;曲士不可以语于道者,束于教也”(《秋水》:455)。
自我之外的世界万物,更是不可知和不可控的在先、在外的状态,即“物已死生方圆,莫知其根也,扁然而万物,自古以固存”(《知北游》:595-596)。社会人事中也有很多不可逃避的事情,庄子借“仲尼”之口将其归纳为两种“大戒”,即“其一,命也;其二,义也。子之爱亲,命也,不可解于心;臣之事君,义也,无适而非君也,无所逃于天地之间”(《人间世》:125-126)。庄子在文章中塑造了各种“残缺意象”,即王骀、叔山无趾、哀骀它、支离疏、佝偻丈人等身体残疾和形貌丑陋的人,试图将主体置于一种与身体疏离的语境中进行讨论,由此获得对于主体的新的认知。当主体在面对这些无可奈何的局面的时候,存在着深深的焦虑和无力感。这是一种扑面而来的“势”,一种难以摆脱的困局,如此,那种充满主体意识(主体性)的传播努力便显得勉为其难。
其次,世界更多的是不可知,而“知”总是暂时的、相对的,人类的认知对此无能为力。在庄子看来,世界是一种“大”的状态,这会让俗世之人感到困惑,比如天地是很大的,它支撑着世界的运转,所谓“大块噫气”,一般人是看不到、听不到、感知不到的(《齐物论》:36-39);而人又总是昧于众俗,故而“大惑者终身不解,大愚者终身不灵”(《天地》:363);“高言不止于众人之心”(《天地》:365),人们跳脱不出世俗的窠臼;甚而“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紸箧》:287),当窃国者连度量、仁义等评价标准也都通通重构,普通人是无法洞察的。庄子将不加质疑的人称之为“芒者”,“芒”,“暗昧也”,是“举世皆惑”的一种状态(《齐物论》成玄英疏:48),而圣人的“明”则是明确地意识到这种“芒”。人类的无知往往始于自我中心主义,常常“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因为“自彼则不见,自知则知之”(《齐物论》:51-52);人类总是处于既有的思维定式当中,“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无用之用也”(《人间世》:149),因而看不见“不材之木”“不龟手之药”“大瓠之种”等的“大用”。故而,从认知的角度来看,人类总是处于“其所言者,特未定也”的不确定状态,无论说还是不说,人言还是鸟语,都很难有一个根本的支撑(《齐物论》:49-50);不可知也是世界的常态,因而常常体现为混、泯、寂、漠、无言、茫然等状态。这就打破了以自我为中心的本体论(Ontology)假设,从而回到一种整体境域中进行认知,承认世界远远超越于自身的认知能力,保持一种“无知”而“旷然无不任”(《齐物论》郭象注:74)的态度才是最高境界。
再次,人与人、人与物作为相互差异的实体,其沟通将存在种种无法逾越的障碍。人类世界总是处于“我-你-它”的关系状态当中,彼此之间是一种相互外在的存在;只不过人与人之间可以通过语言进行沟通,人与物之间则缺少语言的沟通。庄周与惠施的“濠梁之辩”讨论的人是否能够知道鱼的快乐的问题,可分为两个层次:一个层次是人与人,(庄周与惠施)是否能明白对方的快乐;另一个层次是人与物(庄周与鱼),庄周是否能体察鱼的快乐(《秋水》:492)。叶公子高在承担外交事务的时候就面临着传播的焦虑,因为外交事务事关重大,而且对方表面恭敬而内心怠慢。这导致他担心不成功会面临人祸;成功了也会经受身心煎熬。而“仲尼”给出的建议是“传其常情,无传其溢言”,因为过分的言辞必然导致喜怒而产生怀疑,而言辞是最容易片面失当的,因而主张“托不得已以养中”(《人间世》:123-131)。对于基于“不得已”的“安命”态度而获得的“养中”境界,其效应被郭象注曰“接物之至者也”,被成玄英也疏为“应物之至妙者乎”。
对于卫灵公太子这样残暴成性的统治者,作为老师的颜阖该如何对他进行引导?放纵他会危害国家,而试图规范他则自身会遭到危险。对此,遽伯玉提出的解决办法也类似于前述“仲尼”的意见,那就是“形莫若就,心莫若和”;不过仍然需要保持分寸,不能太过,即“就不欲入,和不欲出”,如此才能做到通达(“达”)而行动上没有过失(“无疵”)(《人间世》:132-133)。至于对具体话语内容的体悟,无论是读书还是传授技艺,都是很难以言传意的,因为“视而可见者,形与色也;听而可闻者,名与声也”,因而古人之书不过是“糟粕”。做车轮的工匠“轮扁”也很难将自己的技艺传授给自己的儿子。因为,形、色、名、声只不过是感官层面的符号能指,要进入到符号所指中,则是微妙玄通的;就砍削车轮的技艺而言,其中动作的轻重缓急,则需要“得之于手而应于心,口不能言,有数存焉于其间”(《天道》:394-396)。而具体而微妙的意义(“道”)是超越话语层面而存在的,是“可传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见”的(《大宗师》:198)。无论是从人与人以及人与物的相互外在性,还是传播中的复杂关系对人构成的压迫,以及意义传递的困难,都可以看到传播主体的疏离性困惑。
总之,人类处于这个先在于它的世界,总是被诸多因素所决定而处于一种无可奈何的困局当中,人的主体性显现是极为有限的。对于人的认知能力来说,世界更多呈现为不可知的状态,因而意识到自己的无知也是一种大智慧,而承认“无知”正是一种主体性消解的状态。就具体的传播实践来说,主体之间不仅存在着各种间距(écart),而且具体的意义是微妙而不可传递的,因而传播常常处于只能意会而不能言传的玄妙状态。是什么在阻碍主体与世界的趋近呢?
二、外重与内拙:客体纠缠与主体冲突
在庄子看来,主体总是处于撄、撄宁、摇、荡之中,呈现出物、役、陷、溺、累等主体陷落的状态;主体间也常常出现争、斗、辩、夺等冲突,从而“道术将为天下裂”(《天下》:869)。在此,主客之间和主体之间总是坚实地彼此对立,并且互相纠缠,这反而给彼此带来了危害。那么,主客体之间以及主体之间是如何纠缠在一起的?
第一,作为一种世俗的观念,“以貌取人”常常使得人们陷入到肉身表象的纠缠里,从而阻碍彼此的宽容与接纳。即使是那些自称追求高贵精神的人,也总是会被无意识地卷入到世俗的价值观里。郑国大夫子产看不起他那残疾的同门申徒嘉,从而违背了自己追求的“形骸之内”的精神交往原则,落入以貌取人的“形骸之外”的庸俗境界里(《德充符》:158-162)。人类是一种精神性的存在而不仅仅是肉体,庄子使用一个寓言对此进行推理:一群猪仔吮吸刚刚死去的母猪的奶汁,不一会就惊散逃离,因为它们意识到母猪已经死了。可见,小猪们爱它们的母亲,并不是爱它的肉体,而是爱它的精神(《德充符》:168-169)。
美并不是肉体性的,而是精神性的。对于朝夕相处的店老板的“妾”,周围的人们已经是美的看不见美,丑的看不见丑,因为“其美者自美,吾不知其美也;其恶者自恶,吾不知其恶也”(《山木》:567),即天长日久,肉体的美与丑都会习焉不察,精神性的东西反而得以彰显。与此类似,庄子讲述了很多身体残疾的人,精神上却很迷人的故事,阐述了“德有所长而形有所忘”(《德充符》:174)的道理,明确倡导人类交往的核心其实就是“精神交往”,并以此克服肉体的障碍。肉体是一种客体化的存在,它并不是主体的根本性存在,但是却始终搅扰着人的安宁,并影响着相互间的关系。只有“精神”才会“四达并流,无所不极”(《刻意》:440),以此穿透主体间的心灵,涵纳万物的存在。
第二,传播主体之间的相互客体化,导致彼此关系纠缠不清,从而产生冲突。因此庄子说“故有人者累,见有于人者忧”(《山木》:547),并举例说,自己的船被另一艘空船碰撞,即使心急的人也不会生气;但是假如那艘船上有人,则必然会大声呵斥责骂。生气和不生气的原因,仅仅就在于有人和无人。在此,主体并没有将“空船”纳入客体范围进行意向性投注,因而不以为意;而“人”的存在却无可回避地纠缠着主体的情绪,彼此之间非要争执是非对错,呈现了一种彼此试图压制的局面。当然,在庄子的逻辑里,不但有自我被客体化他人所“累”的一面,也还有一种自我客体化以迎合他人的“忧”的一面。主体之间的疏离程度,也决定着语言使用的多少和客体化的程度,比如,踩了陌生人的脚,需要道歉认错;踩了兄弟的脚,稍稍安慰一下即可;踩到父母亲的脚则不需一言(《庚桑楚》:652)。越是主体融入的至亲关系,越不需要言辞;越是陌生的主客关系,越需要言辞以维系,因而庄子说“至仁无亲”,即亲人之间是一种主体融入而不是主客分离的状态。人们对于“功”“名”的追求也是主体被客体化的诱因,比如孔子被围困于陈蔡之地,皆因其门徒众多而被误认为是阳虎(《山木》:550),孔子与此类似故事还有“伐树于宋”“削迹于卫”“穷于商周”等,其社会困境的根源在于“功”与“名”;“龙逢斩,比干剖,苌弘紽,子胥靡,故四子之贤,而身不免乎戮”,灾祸的根源正在于其汲汲于“贤”,因而被客体化地加以处置(“戮”)(《紸箧》:282)。
第三,诸多的客体吸引着人,搅扰着人心,并造成人与人的冲突,成为某种欲望的“价值客体”(objectsdevaleur)。因为“在获取意义的路途上我们所遇见的只能是规定客体的价值,而不是客体本身”[3](P19),客体只是价值的载体而已,故称其为“价值客体”(objectsdevaleur)。在“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的故事中,庄周也试图在栗园中手持弹弓打鸟,因此没有发现园主人已经到了跟前,由此被唾骂和驱赶(《山木》:563-565)。在此,行动者相互之间彼此欲望着,并由于欲望的对象而忽视了自身的危险处境,即蝉欲望着树荫,螳螂欲望着蝉,黄雀欲望着螳螂,庄周欲望着黄雀,最终彼此都忽视了自身的危险处境。其原因在于“物固相累,二类相召也”,成玄英疏曰:“故知物相利者,必有累忧”“有欲于物者,物亦欲之也”(《山木》成玄英疏:565)。实际上,客体的价值不一样,对人往往会产生不同的影响,比如“以瓦注者巧,以钩注者惮,以黄金注者胮”,因为“有所矜则重外也。凡外重者内拙”(《达生》:521)。正是因为赋予了瓦片、钩带、黄金不同的价值位阶,故而其对于人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构成了巨大影响。这些都是通过价值添加的方式导致的问题,假如能够做到对待生死、断足、钱财等价值客体“视丧其足犹遗土”(《德充符》:154),那么客体也就不会对人自身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构成任何影响。
第四,对于其他诸子尤其是儒家提出的一套关于智慧、道德、仁义、名声等的价值观,庄子也将其作为社会混乱的根源加以批判。“德荡乎名,知出乎争。名也者,相轧也;知也者,争之器也。二者凶器,非所以尽行也。且德厚信筙,未达人气;名闻不争,未达人心”(《人间世》:110)。面对暴君的说服就存在两个方面的问题:其一,“德”“知”“名”等价值正是灾祸根源;其二,对方不信任,在心理上不接纳,反而会陷于被动。因此只有做到“心斋”之后的“虚室生白”才能实现“吉祥止止”“鬼神将来舍”(《人间世》:122)的“镜照”效应,做到“物来而顺应”[4](P460)。这并不是一种骑墙派的作风,而是遵循自然之性的“有主而不执”(《则阳》:728),即不能执着于是非、对错、道德、仁义等价值说服,因为对方也存在“执而不化”(《人间世》:115)的问题,两种价值之“执”的对撞是无法协调的。那种强制地以某种价值改造社会的做法,犹如“待钩绳规矩而正者,是削其性者也”,因为“凫胫虽短,续之则忧;鹤胫虽长,断之则悲。故性长非所断,性短非所续,无所去忧也”(《骈拇》:259)。正是诸子百家学说的价值纷乱,导致“天下大乱,贤圣不明,道德不一,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而且“百家往而不反,必不合矣”(《天下》:867,869),由此造成了辩、争、斗、夺等冲突不止的局面,最终破坏了“性”、“自然”、“天”、“道”等原初起点的根本性和完满性。
总之,主体并不是完全自足的,而是被客体或者其他主体所规定和纠缠。黑格尔就认为自我意识“本质上是从他物的回归”[5](P116),不过,这种回归是通过“发现它自身是另外一个东西”的自我丧失和“在对方中看见它自己本身”[5](P123)的扬弃的双重性而得以实现的。拉康也认为主体是一种无意识的主体,是像语言一样被结构的,“无意识,就是他者的话语”[6](P268);马丁·布伯也认为“‘我’不能独立存在,它或附属于‘我-你’或附属于‘我-它’”[7](PP.1-2),即“我”是被“你”和“它”所决定的。对于客体的纠缠,庄子一方面看到了客体的价值性及其虚妄性,这是一种认知层面的洞识;另一方面则看到了主体性层面的阻碍,即主体总是被客体吸引而出现了认知的偏执,从而阻碍着彼此的接纳。因而他主张采取的是“不累于俗,不饰于物,不苟于人,不忮于众”(《天下》:876)的顺应姿态,最终通过主体性消解的逻辑做到“乘天地之正”(《逍遥游》:16)“和以天倪”(《寓言》:758)的和合状态。

三、齐物与见独:解除客体纠缠的路径
客体往往是依赖于主体观看的角度而被意识到的,故而“以道观之,物无贵贱;以物观之,自贵而相贱;以俗观之,贵贱不在己”(《秋水》:465)。但是,主体往往囿于一定的时间、空间、观念、符号等局限而无法洞察“万物齐一”道理,因而就会陷于无限的是非、对错、美丑、道德、仁义等的评判当中,而这种评判则是一种“分”“判”“析”“察”。持有这种观念的,也就仅仅只是“不该不遍”的“一曲之士也”,“寡能备于天地之美,称神明之容”(《天下》:868-869)。如此将客体片面化处理,正是导致客体处于“杂”“乱”“骈”“淫”“偏”“蔽”等“失道”状态的根源。在此,客体已经从它所属的整体世界中被离析出来,仅仅是为了主体认知和控制的需要而失去了其生命的活力,因而“其分也,成也;其成也,毁也”(《齐物论》:57)。
针对主体与自我、自然、世界以及他人的关系,庄子发现了客体总是纠缠不清,解决问题的办法就是“齐物”,即齐万物、齐生死、齐是非、齐贵贱、齐大小。而物之“不齐”的原因正在于语言,“物谓之而然”(《齐物论》:55),即是非、美丑、生死、贵贱等正是在语言二元切分基础上“可乎可”“然于然”的结果;“不言则齐,齐与言不齐,言与齐不齐也,故曰无言”(《寓言》:760),庄周主张通过“无言”以破除语言的束缚(“荃”),以能做到“齐物”。
“无言”并不可能真的是离开语言,而只是一种批判逻辑下的语言反思而已;庄周使用的语言就包括“寓言”“重言”和“卮言”,其中,“以卮言为曼衍,以重言为真,以寓言为广”,这也被其称之为“谬悠之说,荒唐之言,无端崖之辞”(《天下》:888-889),庄子正是利用这种非常规语言以突破常规语言的局限性,从而实现对于客体的准确把握。另外,庄子还提到两种语言逻辑,即“反衍”和“谢施”。“反衍”是为“贵者反贱,贱者复贵”;“谢施”是为“物或聚少以成多,或散多以为少,故施用代谢,无常定也”(《秋水》成玄英疏:472);与此相对,“曼衍”则被郭象注为“无极”,成玄英疏为“犹变化也”(《齐物论》郭注、成疏:88),是一种阳光般生生不息的无穷涵摄力(“卮言日出”)。
上述语言并不是一种逻辑的语言,而是一种充满想象力的语言,“要把握万物相通的整体,就要靠想象;否则,在场的与不在场的之间、显现的与隐蔽的之间、过去的与今天的之间就永远只能相互隔绝”[8](P12);中国画论里的“出-没”“掩-映”“有-无”的审美方式,正是通过符号引发的想象以抵达无限的世界。庄子试图通过充满想象的语言,使得主体能够超越客体的纠缠,返回到一种自然、无待的自由状态。
庄子认为,在世俗的生活当中,辩论或者理智并不能够获得真知;仅仅是为了争胜,反而遮蔽了人们的认知,导致传播问题丛生。主体其实总是处于一种“芒”的状态,所谓的认知也不过就是“随其成心而师之”,故而人人都以为掌握了真知;而没有内心的标准(“未成乎心”),也是无法进行判断的。言语并不像自然天籁那样有天在主宰,因而是是非非都是不确定的,所谓的辩论,也就与小鸟的鸣叫没有什么区别。“道”正是被世俗道德、偏见、功名以及言辞所遮蔽,因此才出现了儒墨等百家争鸣的“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相互攻击的局面。从本体论的角度来看,“事物”就是其本身,根本上是“天”作用的结果,所谓彼此,无非就是视角不一样,即生与死、可与不可、是与非等实际上皆为一体(《齐物论》:48-52)。
生死这样界限分明的“事实”,在庄子看来实是语言切分的结果;生死就像白天黑夜(《大宗师》:193;《至乐》:500),是从“无”(未生)到“有”(生)又回归于“无”(死)的自然一体过程(《大宗师》:206)。语言强行将这个自然一体过程分为两个阶段,而人类自以为是地给“生”添加正面价值而给“死”添加负面价值即好生恶死导致了人的喜怒哀乐。庄子却能够做到妻子死了“鼓盆而歌”(《至乐》:498)而“死生无变于己”(《齐物论》:78)。首先,死生不在自己控制范围,“死生,命也”(《大宗师》:193),是“造化”的作用;其次,死是不可知的,我们怎么知道生不是“惑”而死不是“弱丧”呢(《齐物论》:83)?因此“死生存亡,穷达贫富,贤与不肖毁誉,饥渴寒暑,是事之变,命之行也”,假如能够做到“不足以滑和,不可入于灵府”,便能达到“才全”(德全)(《德充符》:170)。
这种文化符号二分的“价值客体”建构常常导致欲望的唤起,而“其嗜欲深,其天机浅”(《大宗师》:184),欲望必然遮蔽人类的多重视野和认知,主体便被卷入其中而无法自拔。一旦做到了“外天下-外物-外生”之后的“朝彻”,便能够“见独”(《大宗师》:203);所谓“见独”即“无与为对”之“道”[9](P147),“莫得其偶”“德其环中”(《齐物论》:53-54)。这就抛弃了文化的禁锢从而洞察世界的根本,最终做到“安时而处顺,哀乐不能入”的“悬解”(释文:“无所系”)而不再“物有结之”(钟泰:“物情缠绕”)(《大宗师》:209)。这就获得了无待、开放而自由的主体心灵以面对世界,趋向“指与物化而不以心稽,故其灵台一而不桎”(《达生》:536)的心与物、心与心的圆融状态。
正是因为主体不被客体所纠缠,反而增进了主体间的关系,因此“百里奚爵禄不入于心”而受到秦穆公的赏识;“有虞氏死生不入于心,故足以动人”;不拘小节的画家才是真画家;姜子牙无钩而钓,却能得到文王重用(《田子方》:582-583)。客体作为一种中介,总是在阻碍主体与主体、主体与客体的趋近与交融,因而“君子之交淡若水,小人之交甘若醴;君子淡以亲,小人甘以绝。彼无故以合者,则无故以离”(《山木》:555-556)。同样,传播实践当中,当对象被作为亲人、朋友、熟人、陌生人、敌人等“身份”方式加以“外在”地、“经验”地对待的时候,它已经被客体化了;按照马丁·布伯的观念,这就是一种“我-它”的主客关系而不是“我-你”的主体间对话关系[7](PP.3-4)。
故而庄子说,要说“仁”,则虎狼也有“仁”,它们也懂得爱自己的孩子;而“至仁”则是建立在“忘”的基础上的“至仁无亲”,因为“至仁尚矣,孝固不足以言之。此非过孝之言也,不及孝之言也”;因此“以敬孝易,以爱孝难;以爱孝易,以忘亲难;忘亲易,使亲忘我难;使亲忘我易,兼忘天下难;兼忘天下易,使天下兼忘我难”;再推而广之则“至贵,国爵并焉;至富,国财并焉;至显,名誉并焉。是以道不渝”(《天运》:401-404)。当通过“忘”“无”“捐”“取”等功夫,使得功名、财富、亲疏等价值不被赋予客体,客体也就不成其为“客体”,因为它没有了特殊的价值,就不入于胸臆,欲望无由产生,主体也就不会与世界相疏离,最终便会达致“入兽不乱群,入鸟不乱行”(《山木》:554),“登高不栗,入水不濡,入火不热”的与天地和合的“真人”境界(《大宗师》:183)。同样的道理被马丁·布伯表述为“一切媒介皆是阻碍。唯有摒弃一切媒介,相遇才会发生”[7](P10)。
四、坐忘与物化:主体性的消解与主客交融
客体以及客体价值的消解当然是主体趋近世界的重要方式,但在庄子看来还不是根本的方式;而“吾丧我”中对“我”的消解才是最为根本的,如此才能实现主体与客体的交融,即通过“坐忘”实现“物化”。所谓“坐忘”,即为“堕肢体,黜聪明,离形去知,同于大通”(《大宗师》:229),这是对于自我的身体、耳目、智慧等现实存在方式的主动消解,准确的表述应该是“吾丧我”的一种“忘我”。这也就是对主体性的消解,即通过掏空主体性而实现主体的完全自由与敞开。
综合前面小节的论述,这种“忘”是从客体之“忘”而最终达致“吾丧我”的“忘我”,是以“外天下-外物-外生”(《大宗师》:203),“忘仁义-忘礼乐-坐忘”(《大宗师》:228-229),不敢怀“庆赏爵禄-非誉巧拙-四枝形体”(《达生》:534)等方式逐步推展开来的过程,最终落到对“我”的消解上。有学者认为“我”是现实中被物论所遮蔽的自我(小我,俗我,识神),而“吾”则是人本来面目的本我(大我,道我,元神);俗我类似于米德的“主我”(I),而“道我”类似于“客我”(me)[10](PP.61-76)。但是,米德(GeorgeHerbertMead)认为“其他人的态度构成了有组织的‘客我’”,而“主我”则是通过对“客我”的“反应”或“反作用”而得到界定的[11](PP.193-194)。因此,米德的“客我”是社会性和经验性的自我,它更接近于庄子的“我”(俗我)而不是“吾”(道我),而“吾”也不是像米德所说的那样是“主我”对“客我”的反应,而是对“形态的我”和“情态的我”的无限纠缠的消解。因为“只有‘丧我’,使‘吾’透显,才有宽容,才得自在-自由”[12];它是不同于“丧己于物,失性于俗”(《缮性》:452)的主体陷落(reification),而是保持“物物而不物于物”(《山木》:543)、“不与物迁”(《德充符》:152)的独立、自由与无待。
首先,是对于感官之“我”的消解,如此才能摆脱感官对象对于主体的扰动。客体对主体的干扰一方面是因为客体被赋予价值;另一方面则是因为主体的某种感官性存在。其中,从人之常情来看,“目欲视色,耳欲听声,口欲察味,志气欲盈”(《盗跖》:807),有感官必有“欲”的产生,但是,耳、目、心因“有意则无涯”(郭象注),即因其意向投注而被裹挟进客体,由此造成诸多问题(“怠”)(《徐无鬼》:699),比如“五色乱目,使目不明”“五声乱耳,使耳不聪”“五臭熏鼻,困?中颡”“五味浊口,使口厉爽”“趣舍滑心,使性飞扬”(《天地》:419)。而感官消解就是需要通过“心斋”“坐忘”“凝神”等方式做到“形如槁木”“遗物离人”(《齐物论》:35;《达生》:518;《田子方》:576)的身体疏离,以实现能听见“天籁”(《齐物论》:36),“以神遇而不以目视,官知止而神欲行”(《养生主》:97-98)的心灵自由之境。当然,日久天长的适应以及不断的熟练,也能够忘掉感官束缚,故而“忘足,屦之适也;忘要,带之适也;知忘是非,心之适也”(《达生》:536);对于从小生活在水边的泳者,就能够做到“与齐俱入,与汩偕出,从水之道而不为私焉”(《达生》:532-533)。因此,通过感官的消解,一方面主体获得了心灵自由之境;另一方面,主体得以充分融入客体当中,即“大同而无己”(《在宥》:313),郭象将其注为:“有己,则不能大同也”。
其次,通过欲望和智识的消除克服自我心灵的束缚,从而做到“圣人怀之”的包容性(《齐物论》:70)。欲望常常会堵塞人的认知能力,影响到心灵的开放,因为“其嗜欲深者,其天机浅”(《大宗师》:184);而庄子甚至拒绝机械对于人力的辅助,主要是警惕“机心”对人心的遮蔽,他借圃畦丈人之口说:“有机械者,必有机事;有机事者,必有机心。机心存于胸中,则纯白不备;纯白不备,则神生不定;神生不定者,道之所不载也”(《天地》:352)。因而需要“洒心去欲”“少私而寡欲”(《山木》:545-546),“君子不可以不刳心焉”(《天地》:330),才能开放心灵,获得趋近世界的根本之“道”。小我之“私”是一种“畛域”,它是无法做到“兼怀万物”,应而“无方”的,只有做到“无私德”“无私福”才能实现“无拘而志,与道大蹇”(《秋水》:472-473)。而“私”即是一种人为,它往往会造成对自然对象(“天”)完整性的破坏(“牛马四足,是谓天;落马首,穿牛鼻,是谓人”),故而要“反真”就需要做到“无以人灭天,无以故灭命,无以得殉名”,因为“天在内,人在外”,即人为是外在强加的,并不是天然如此(“内”)(《秋水》:476-477)。
所谓“兼怀万物”可以从三个方面去理解:第一,需要一种谨慎的态度,即“言察乎安危,宁于祸福,谨于去就,莫之能害也”,由此,各种神人具有的“火弗能热,水弗能溺,寒暑弗能害,禽兽弗能贼”等等神通便很好理解了;第二,采取“自我”逻辑在后的被动策略,而非“自我”逻辑在先的主体支配性位置,因而其处世的方式为“因”“应”“趁”“凭”“任”“顺”等,做到“不为福先,不为祸始,感而后应”“不思虑,不豫谋”(《刻意》:436-437);第三,“澹然无极,而众美从之”(《刻意》:434),通过心斋剔除坚实的自我才能实现“唯道集虚”,同时放弃耳、心等感官信息接收方式而“听之以气”,才能做到“虚而待物”(《人间世》:119)。
再次,通过想象力的拓展克服小“我”(主体性)的狭隘性,以实现对于他人或者他物的无限接纳。《庄子》通过夸张、寓言、假设等修辞方式,使其行文充满着无穷的想象力;而这种想象力的展开,便使得其思考大大突破了经验和逻辑的局限性,从而看到广阔世界的可能性。当人类“自我”超越到经验和逻辑之外的时候,它便克服了小“我”的认知狭隘性,最终得以拥抱更加广阔的世界。比如人在万物和世界中的渺小,即为“号物之数谓之万,人处一焉;人卒九州,?食之所生,舟车之所通,人处一焉;此其比万物也,不似毫末之在马体乎”(《秋水》:458);从人类的角度去看蜗牛角上的两国战争,就会发现它们是可笑而无意义的,从宇宙的角度来看魏国与齐国的战争,不过也是如此(《则阳》:715)。
因此,一旦参透“我”的渺小,战争的冲突、利益的争夺、彼此的控制都是可笑而无意义的。醉酒之人正因为意识不清醒,处于“乘亦不知也,坠亦不知也”的忘我状态,“死生惊惧不入乎其胸中,是故?(注:干触)物而不訴(注:恐惧)”,因而与外在的世界处于一种“不逆”的顺应之态;推而广之,则“圣人藏于天,故莫之能伤也”(《达生》:515-516)。再将视野推展开来,可以看到藏小于大则可以“遁”,但是“藏天下于天下而不得所遁”(《大宗师》:196)。当我们纠结于人类或者个体的“我”的视角,则“自细视大者不尽,自大视细者不明”(《秋水》:462)。当摆脱了人类的视角,“我”甚至已经无限缩小以至于“无我”,主体便是一种虚空而敞开的“至大无边”状态,那么所谓的显与藏、大与小等词语便不再有效,这反而能够让他人、万物与主体和谐共处。
人与世界、万物以及他人之间的关系,在庄子看来是一种“物化”的过程,是在对“我”的消解的基础上进行的,“同于大化”的过程,即“古之畜天下者,无欲而天下足,无为而万物化,渊静而百姓定”(《天地》:330)。诸多解释者始终从“对象”本体论角度来解释“物化”,比如成玄英认为是“新新变化,物物迁流”的“物理之变化”(《齐物论》成玄英疏:93);陈鼓应认为是“万物之转化”[13](P102):日本学者池田知久则认为是“‘物’的死与转生”[14](P269);王向清、周蓉认为是“一体流变,更生成始”[15]。
实际上,认识“物”的变化并不是庄子的目的,而处理“人”与“物”(他人)的关系才是其目的,因为庄周梦蝶本质上谈的是庄周与蝴蝶不分的一体化问题(《齐物论》:93);生死的“物化”谈的是如何融入宇宙万物的问题(《天道》:375);巧匠工翺的“指与物化”即是一种人与物的冥合状态(《达生》:536)。因此,“物化”的问题更应该是“人”与“物”(他人)的“间性”问题,而不仅仅是“物”的本体问题,因为从《庄子》整个思想脉络来看,是从真知论、齐物论到安命论、逍遥论[16](P142),最终指向一种“物我交融”“天人合一”的生命境界[17]。庄子所讲的“物化”不同于批判哲学里的“物化”(reification);后者是一种“丧己于物”(《缮性》:452)的主体陷落状态,这恰恰是庄子需要通过“吾丧我”加以祛除的。
五、结论:“吾丧我”的传播学意蕴
正是通过“吾丧我”对“主体性”(“我”)的消解,客体不再纠缠主体,主体也不再把自己作为“客体”来坚守;当自我、他人与世界跳出“价值”束缚的时候,它们也便仅仅是“物”,所以彼此间“物化”的过程就是各美其美的“自化”过程,也是彼此融合的“道通为一”的过程,由此,传播的冲突也就不复存在了。而“物化”逻辑中,关键是如何看待“物”。这包括两个视角:第一个视角,是本文第二部分处理的价值消解的非客体化(“物”),从而避免主体陷落到客体当中,也避免将自我和他人作为客体来对待;第二个视角,是第四部分处理的通过“忘”去除人的身体、欲望、存在等对“我”的坚执,从而使得主体获得自由、开放与敞开的境界。在“朝三暮四”的寓言中,猴子看起来幼稚的原因在于,它们不知道“3+4”和“4+3”其实是一样的。而在人类的传播实践中,他们建立了数字基础上的可通约性,因而不会在两种组合上计较(“怒”)(《齐物论》:58-59)。当然,庄子并不是在数学同一性的抽象基础上讨论世界的可通约性,而是在“齐物”与“物化”的视角下展开世界的同一性。庄子正是通过“吾丧我”的过程,在“物”这个层面找到了主体与他人、世界的可通约性,所以才能实现“物化”。
主体并不等同于人的身体、欲望和存在,而是通过对这些外在方式进行“吾丧我”操作之后,体验到一种“同于大化”的“物化”过程,在此,主体反而获得了一种无限敞开的生生不息的活力。其实,主体完全可以理解为“虚静、恬淡、寂漠、无为者”,是一种“圣人之心”的境界,这类似于“天地之鉴也,万物之镜也”(《天道》:371)。这个“镜子”隐喻经常出现在中国文化的哲学思考里,反映的正是因为主体性的消解,它才能照见万物,并让万物呈现出它们的本来面目,而不是通过主体去切割万物(他人)和支配万物(他人)。这与西方文化中的“镜像”隐喻通过镜子看到自己是截然不同的。
而西方传播理论里的说服、解放、认同、移情、对话等等逻辑,其前提基本都是建立在主体性和主体间性之上的,体现的是一种主客对立思维模式和“有我之境”。而当主体的实体性(主体性)被破除,主体敞开后便是镜子般的“无我之境”,这是一种“以物观物”而“不知何者为我,何者为物”的融合境界[18](P1)。当西方传播理论执着于观照客体(管理、批判)和主体间性(对话)的时候,实际上是将“主体”作为一个不加追问的预设前提。而从中国文化的哲学上“忘我”之后进入艺术当中;从家庭中父母为孩子的无限“忘我”牺牲当中;从人与人之间强调为他人着想的“忘我”当中,我们都可以看到,正是“吾丧我”的逻辑使得主体融入到了世界当中,并以此实现其伟大与崇高。这正是华夏传播研究可以为世界传播研究提供的新视野。
参考文献
[1]李红.老子思想的符号逻辑及其传播伦理[J].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10).
[2]约翰·杜翰姆·彼得斯.对空言说:传播的观念史[M].邓建国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7.
[3][法]A.J.格雷马斯.论意义(下)[M].冯学俊,吴泓缈译.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5.
[4]程颢.答横渠张子厚先生书[A].程颢、程颐著,王孝鱼点校.二程集[C].北京:中华书局,2004.
[5]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上卷)[M].贺麟,王玖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
[6]黄作.不思之说——拉康主体理论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
[7][德]马丁·布伯.我与你[M].徐胤译.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18.
[8]张世英.进入澄明之境:哲学的新方向[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9]钟泰.庄子发微[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10]谢清果.内向传播视域下的《庄子》“吾丧我”思想新探[A].诸子学刊(第十辑)[C].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
[11][美]乔治·赫伯特·米德.心灵、自我和社会[M].霍桂桓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2.
[12]陈静.“吾丧我”——《庄子·齐物论》解读[J].哲学研究,2001,(5).
[13]陈鼓应.庄子今注今译[M].北京:中华书局,2011.
[14]池田知久.道家思想的新研究[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9.
[15]王向清,周蓉.《庄子》“物化”思想论析[J].哲学研究,2015,(6).
[16]刘笑敢.庄子哲学及其演变(修订版)[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
[17]蒋丽梅.物我感通,无为任化——庄子“物化”思想研究[J].中国哲学史,2015,(3).
[18]王国维.人间词话[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注释
本文所引庄子原文及其注疏依据版本为:刘文典《庄子补证》,中华书局2015年版。引用格式为“《篇名》:页数”;成玄英注疏则标注为“《篇名》成玄英疏:页数”;郭象注则标注为“《篇名》郭象注:页数”。
原文载丨《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02期。
名家简介

李红,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符号学、视觉修辞与华夏传播研究。兼任华夏传播研究会副会长;中国新闻史学会文化与符号传播学研究委员会常务理事;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文化与传播符号学分会第一届常务理事;四川大学符号学-传媒学研究所特约研究员;《视觉传播研究》(集刊)副主编。出版专著一部;在《国际新闻界》《现代传播》《新闻大学》等发表CSSCI期刊文章20余篇;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教育部项目,参与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等。
-
【名家说岭南•董兴宝】马戛尔尼使团对广州十三行的记载(1)
2024-05-13 16:44:06 -
【名家说岭南•张培忠】张培忠:让广东文学馆活起来,实现文学和产业的“双向奔赴”
2024-05-12 20:39:12 -
【名家说岭南•赵利平】从文化看饮食的当下与趋向
2024-05-12 11:24:24 -
【名家说岭南·江冰】记住母亲,就记住人生最温暖的部分
2024-05-12 11:13:5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