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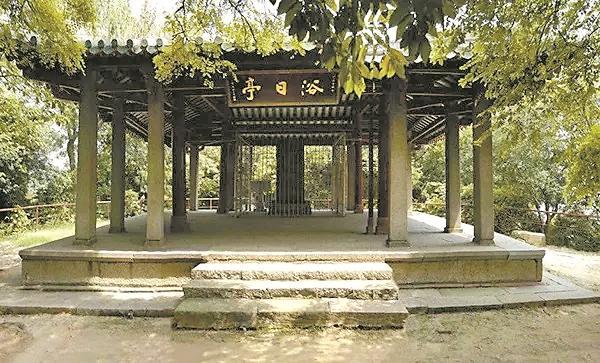
文字整理/羊城晚报记者 黄宙辉 通讯员 颜戴丽
7月9日,第十三届广州学术季“品读诗意花城”开卷广州系列阅读活动推出一场线上直播讲座,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彭玉平为读者讲述有着两千多年历史文化积淀的诗意广州。
在人们印象中,广州的“千年商都”名号实至名归,而现在说它有条件建设一座“诗词之都”,却颇有人感到困惑。对此,彭玉平教授有独特的见解:
岭南文化由弱到强
讲到历史上的诗词之都,我们想起的是洛阳、开封、西安、南京、苏州、上海、杭州、扬州、北京、成都。大家去看中国诗歌史、词史,有大量的诗人词人、大量的优秀作品往往与上述10个城市有关,但很少有人会把广州列进去。所以,建设广州“诗词之都”,有的人可能就有一些困惑:历史上,广州好像难以称为“诗词之都”。
论诗词、论文学甚至论艺术,如果从总体的成就和影响来说,历史上广州确实是一个长期远离文化中心的一个城市。
我用“受容”“包容”和“从容”三个词来概括岭南文化对于北方文化蜕变的过程。
明代以前,是“受容”,接受并消化。唐代的韩愈,宋代的苏轼,这些一流的文学家被贬岭南,带来了中原文化和江南文化的强势文化。岭南人(广州人)低调,也善于学习,虚心地学习这些强势文化。
明清两代,是“包容”。这个时期,北方文化跟岭南文化可以说是“双水并流”,岭南人不排斥北方文化,但也坚持自己的文化。
从近代开始,是“从容”。近代,岭南人反而站在了开放的前沿。他们把自己的原初文化跟开放文化相结合,令近代以来的广东文化后来居上,由南方辐射影响到北方。低调了2000年的广州,从近代以来就不再低调,时代也不允许它低调,这是岭南文化从弱到强的过程。
广州与诗歌缘分不浅
目前,广州要通过建“诗词之都”的方式来复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确实也有着自身的基础和条件。
广州是一个花开四季的城市,哪个季节都有一树一树的花开,这是诗歌的一个境界。广州是一个从容优雅的城市,市民随性随意,慢节奏。这样从容优雅的品格,跟诗歌品格非常接近。此外,广州的市民是非常沉浸在自我世界中的,简单说就是习,从“我的角度”去看世界,而不是从“世界的角度”去看世界,这就是一种诗性。
广州还是一个诗性馥郁的城市,具有悠久的诗歌源流。至少从晋代开始,到南北朝,到唐宋元明清,一直到近代,广州从来没有远离诗歌,或者说在广州历史发展过程当中,诗歌一直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广州这片热土孕育了许多诗人,抚慰了许多失意的诗人,也催生了许多优秀的诗歌。我在这里举一些诗歌史上与广州或广州诗人有关的例子:
南北朝时期的南海人刘删有“岭左奇才”之称,诗文已达到相当的艺术水准。例如他的《登庐山》一诗:“野烟出炉上,山花落镜前。危梁取大壑,瀑布挂中天。”我觉得比大名鼎鼎的李白那首《望庐山瀑布》还要好。
南北朝时期的另一位诗人谢灵运,晚年被贬到广州,后被朝廷处死,他在广州写下了一首《临终》诗:“送心自觉前,斯痛久已忍。恨我君子志,不获岩上泯。”他把人生的绝唱留在了广州。
到唐代,张九龄曾写下《与王六履震广州津亭晓望》:“明发临前渚,寒来净远空。水纹天上碧,日气海边红。景物纷为异,人情赖此同。乘槎自有适,非欲破长风。”
南宋大诗人杨万里作《三月晦日游越王台》:“榕树梢头访古台,下看沧海一琼杯。越王歌舞春风地,今日春风独自来。”记录了他游广州的经历。
再有屈大均、陈恭尹、梁佩兰三位诗人,被称为清初“岭南三大家”,他们与广州有密不可分的关系。这三个人的诗文都写得非常好,其诗风“雄直”,出岭南而享誉全国。
来自历史深处的驱动
虽然从历史上来说,广州要称为“诗词之都”,条件可能确实比不上洛阳、南京、苏州、扬州、西安等地,但不等于广州没有诗心、没有诗性,而恰恰是诗心浓郁,诗性强烈。诗心广州人,诗性广州城——市民拥有的对于这种与诗歌相通的心灵的一种感悟,也带动了整个城市的氛围。
上面所梳理的诗歌,在中华诗歌宝库里其实一点也不逊色,但关于广州的诗歌还非常缺乏宣传、缺乏研究,以至于大家认为广州似乎够不上“诗词之都”。当把岭南诗歌的源流梳理了之后,我们就会觉得广州2000多年的诗歌发展,为建设“诗词之都”提供了历史的支持。广州的历史很丰富,至少其中有重要的一部分是用诗歌化成的历史,传递出特别的广州味道和广州气象。
广州建设“诗词之都”,我觉得既是一种来自历史深处的驱动,也是广州作为当代城市的要求。希望我们广州人能够把自己的城市跟诗歌做更多的联系,不要一味认为广州在古代远离文化中心,就势必与诗歌相隔甚远。事实上,广州历史发展的每一步,都有诗人与诗歌来作注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