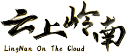

11月9日-10日,2024花地文学榜年度盛典先后在广州、深圳举行。张翎《归海》(作家出版社2023年10月)获评年度长篇小说,特发表其致敬辞、感言、专访——
【致敬辞】
张翎的《归海》把追索历史文化的触角伸向“根”与“路”,既在“寻找别人的珍珠”的过程中直面与疗愈伤痛,也在“打开自己的蚌壳”的同时完成自我重建。
作品借助袁家母女的情感流变叙事,唤醒对个体、对20世纪中国历史的生命记忆。在深海沙砾的碰撞、周旋与流转下,出走与归家的命题已剥离掉陈旧的寻根外壳,浮露出跨越国界民族、省思战争创伤的阔大视野。

【感言】
母语让我找到了非常牢靠的归属感
张翎
非常感谢花地文学榜,这次关注一位海外作家。我是常年生活在不讲汉语的地方,用母语写作,这个过程其实真的是有一点艰难和尴尬。
我在年轻的时候有一种“归属感危机”,经常想自己属于何处?但随着日子慢慢过去,我慢慢长大后,我突然就不那么纠结了,我想因为我找到了一个非常牢靠的归属感,那就是我的母语。无论居住在哪里,走到再远的地方,它跟我有一种血亲关系,是一种永远相互属于的关系。
(文字整理:记者 梁善茵 实习生 蒋晨璐)

【访谈】
记录女性在战争中的创伤与生命力
羊城晚报:《归海》讲述了在加拿大生活的袁凤追忆母亲袁春雨身世的故事,请问写作初衷是什么?
张翎:《归海》是我计划中的《战争的孩子三部曲》的第二部,第一部是2017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的《劳燕》。
为了维生,我在北美做过十七年的注册听力康复师。在我的病人中,有许多经历过战争的退役军人,还有一些是从世界各地涌来的战争难民。我和这群人有过多年接触,从他们身上,我感受到了战争和灾难遗留的长久影响,他们让我思考“创伤”的话题。
战争和灾难是事件,具有时间性,有开始有结束;但战争和灾难带来的后续影响,是事件的“溢出物”(spill over),无人能预测它带来的影响会存留多久。灾难的“溢出物”可以辐射流淌到世界任意一个角落的,正好有一片,就流到了我的工作场所。我就把这些印象和灵感移植到了自己的母语文化中,于是就有了《归海》这部小说。
羊城晚报:《归海》的人物或情节是否存在真实原型?
张翎:和《劳燕》一样,《归海》是基于真实历史事件之上的虚构故事。世界上许多的战争小说都是聚焦在战争本身的,而女性遭受的战争性暴力以及其所带来的深重耻辱感,却没有得到深切的关注和挖掘。
《归海》里的袁春雨,就是一个典型的战争性暴力受害者。她的耻辱是战争带来的,但不止于战争。战争终结之后,强大的社会传统文化偏见一直还存在,受害者往往是无从辩解,一生也无法摆脱的。
袁春雨这个人物和她的遭遇,是许多战争幸存者的故事的缩影,她是完全虚构的,同时又是完全真实的——虚构的是人物,而事件和人物的情感,则是完全真实的。
羊城晚报:您为小说取名为《归海》,英文译名为“当海水相遇”,有何含义?
张翎:水在《归海》里,是与情节息息相关的场景,小说的几个重要环节,都是在水边发生的。
水也是主人公的生活轨道,母女两人从温州的瓯江出发,到东海,到黄浦江,跨越太平洋,最后定居在安大略湖畔——那其实也是我自己的生活轨迹,尽管故事并不发生在我身上。
不同的水域把她们带到人生的不同阶段。水也是一个人文化身份的象征,不同水域的相遇相融也是文化交汇相融的象征。书里有一段跨文化的婚姻,水也隐喻了这段婚姻相互磨合融汇的过程。但更重要的是,我是想通过水的意向来探讨女性生命的力量。
我把我的女性人物比喻成水,不是《红楼梦》贾宝玉嘴里那些玉洁冰清的女儿家那样的水,而是流过最恶劣地形的污泥浊水。她们滋养他人,保守自己,是我心目中具有强悍的生命力的人。
羊城晚报:《归海》是您第一部用英汉双语写作的作品。第一次尝试用英文写作的感受如何?用母语和英语写作,有哪些不同?
张翎:我的本科和硕士都是学英美文学的,用英文写一本通顺的小说想来也不是一件不可能的事。但我从开始写作以来一直坚持使用母语,是因为我觉得只有母语可以抵达我心目中的那个“传神”境地。再熟练的外语,至多也只能做到“达意”。
在用英文书写的时候,整个构思过程就是用英文思考的。除了遣词造句、意象和比喻的不同之外,中文书写中很多烘托和铺垫都是围绕着故事核心层层铺展的,而在用英文书写时,就要考虑如何以英文读者习惯的方式铺陈情节。
另外,由于中文读者和英文读者知识点各有不同,对小说历史背景的详略设计,也是很不相同的。对中文读者很熟悉的历史事件,对英文读者来说可能完全陌生,反之亦然。这些方面的考虑,是用第二语言书写的人必然面临的挑战。
羊城晚报:小说的每个章节都以袁凤与其丈夫乔治的电邮作为开头,您是如何想到采用这种代入第一人称、双线叙事的写作手法?
张翎:电邮部分的内容是最后一稿时才加入进去的,原先这部分是完全缺席的。初稿完成后,突然发现书的第一章以后的全部章节都是“过去时”的,春雨的洋女婿和袁凤的洋丈夫乔治只在开头和结尾里出现过,其他章节里他就被彻底甩出了故事核心。
我感觉到了这个缺陷,于是就以电邮的方式,将现在时和过去时、加拿大和中国两边的故事交织在一起,让乔治始终都在袁凤的“现场”之中。经过这些增写之后,我感觉故事放出去的线都收回来了,人物也饱满起来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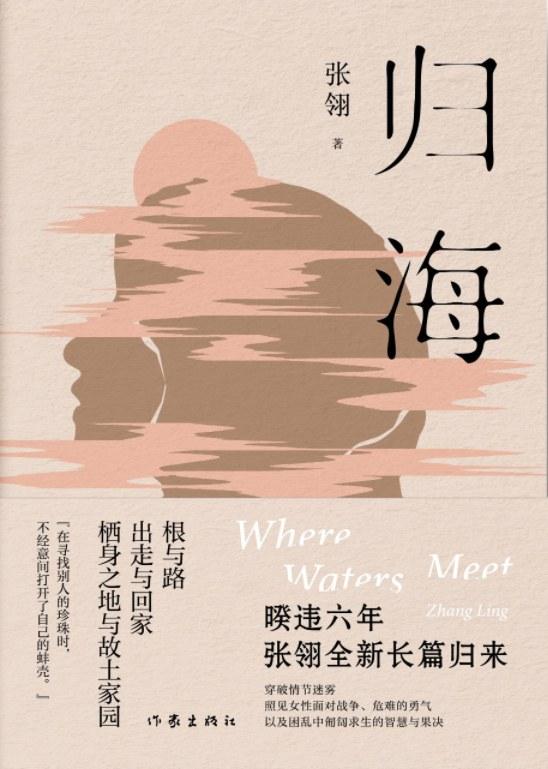
土地因承载历史而血肉相连
羊城晚报:《归海》是“战争的孩子”三部曲的中篇,您对灾难、创伤及其疗愈的书写是否存在一种递进关系?
张翎:在东方文学和西方文学中,对灾难和创伤的书写有时都会过于倾斜在“治愈”的结局上。在东方我们有“凤凰涅槃”的说法,西方也有类似的,比如“杀不死你的,会让你更强大”“每一块乌云都有银边”等等。
好莱坞出品的电影,更是具有招牌式的皆大欢喜结尾。这种让我们感觉到心灵安慰的灾难书写方式,有其正面意义,但不能是唯一的模式。这种模式一旦泛滥,就会成灾,成为廉价的心灵鸡汤,因为我们知道现实生活并不都是这样的。
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创造在废墟上即刻化蛹成蝶、凤凰涅槃的奇迹。那些以水滴石穿的精神,缓慢地经历并走出死荫幽谷的人,还有那些带着身上不能拔出的刺,却以与疼痛共存的信念生活下去的人,同样具备超凡的勇气。每一种经历都值得作家关注书写。
羊城晚报:出版社介绍《归海》是一种跨越国界民族、省思战争创伤的写作,这种超越在今天有何启示意义?
张翎:整个20世纪都是灾难战争不断的世纪,两次世界大战之后,全世界并未赢得长久而稳定的和平,地域性的摩擦一直都在发生,最近的俄乌战争、加沙战乱就是例子。
由于交通和通讯科技的高度发达,战乱对人产生的影响比以前更加容易地“溢出”到世界的其他地区。在这个时候反思过去,对今天和未来有着警示作用。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袁春雨在抗战中所经历的,并不仅仅是往事。她的遭遇,可以使我们理解和关注战争创伤给几代人留下的长久影响,警惕战争的再次发生。
羊城晚报:从《劳燕》到《归海》,您都关照了女性对于战争伤痛和耻辱的隐忍。女作家注定是女性视角吗?女性视角是不是也会造成某种遮蔽或自蔽?如何克服?
张翎:女作家一定会产生女性视角的,这是一个生物学的问题。但女作家不一定完全固定在女性视角上,她还可以有“普世”的超性别的视角。
“遮蔽”和“自蔽”是视野和惯性思维的问题,和性别不一定有关系。对一个作家来说,真相本来就是主观的观察结果,所有世界上的文学表述在某种意义上都是主观的,因为观察的本质就是主观的。
无数个主观视角得到了呈现,事件和记忆就变得丰满而多面。最重要的是要诚实地面对自己的主观,也宽容地接受他人的主观。
羊城晚报:一直以来,“失根”与“寻根”都是众多海外华文作家的书写主题,但您的写作似乎无意过多关注这两种关系的辩证,而是聚焦历史中个体生命的伤痛。为什么?
张翎:这可能和我开始写作的时机有关。
我持续性地发表作品时,已经在海外生活了一长段时间。我在维生的道路上走了很久,当我终于有稳定的收入可以支持写作时,我已经相对安全地度过了文化适应期,移居早期的那些激烈的情绪,已经得到了缓解和平复。
再者,我开始写作时,中国经济已经开始大幅度发展,通讯和交通变得轻省而容易,我可以和国内的亲友们保持密切而即时的联系,也可以随时回国,甚至待一长段时间。地理阻隔不复存在了,就很难再产生余光中年代的那种乡愁。
羊城晚报:小说中的女儿从“寻找他人的珍珠”到“打开自己的蚌壳”,有一种怎样的隐喻?
张翎:女儿在寻找母亲秘密的曲折历程里,认识了母亲身上携带着的历史。而母亲的历史,也是女儿的成长史,这个寻找过程是女儿的自我发现之路(journey of self-discovery)。
对个人历史的发掘可以改变一个人对故土的了解和认识,知道母亲秘密后的袁凤,对故土的认识产生了变化,土地因为承载着历史而变得醇厚、血肉相连。《归海》里有一句话——“故事改变地理”,我想就是这个意思。

写作是我唯一的“定海神针”
羊城晚报:《归海》创作过程顺畅吗?您日常写作的状态是怎样的?
张翎:还算顺畅。一般来说,当我做完案头调研,写出故事大纲的时候,长篇小说就已经完成了一半。
在处于写作状态时,我一般早上醒来(其实已经接近中午),不洗漱不吃早饭,立刻坐下来开始写作。写一段落,再吃个早午饭,稍事休息,午后再写两三个小时,就收工了。晚上不再做“输出”的事,只做休息和“输入”,比如看电影看剧读书,或者和朋友吃饭聊天。
我一天写作的时间不长,从不干涩地写,一旦感觉滞塞,立刻就停下来,等待着灵感再次找到我。每天也不把灵感写完,留一口气给明天。
羊城晚报:您曾经说过写作是您的“自救”,能否展开谈谈“自救”背后的含义?
张翎:年轻时说“自救”,是觉得自己被倾诉的欲望逼到墙角,不抒发不行。
现在说“自救”,是有感于世界局势的动荡不安。在如此分裂动荡的大时代里,写作是我唯一的“定海神针”,保护我不被恐惧和不安吞没,让我在遮天蔽日的不确定中,找到一样确定的事,能够不被眼前的纷乱所动摇疑惑。
羊城晚报:您此前说过在创作《劳燕》时已有写“战争的孩子”三部曲的想法,如今是否已在进行第三部的写作?预计何时推出?
张翎:最近去东非待了一个多月,有很多冲击和灵感滚滚而来,会先完成一部关于非洲的散记,然后回到第三部的写作。
羊城晚报:您的作品读者主要分布在哪些国家?在海外写作会不会感到寂寞?
张翎:流通汉语的国家和地区应该都有我的读者吧,我所居住的多伦多城市的图书馆里,就收藏着很多我的书。我很习惯长时间的独处,一个有事情做的人是不太会感受到孤独的。不是因为不孤独,而是因为没时间感受孤独。
羊城晚报:在《金山》中塑造“金山伯”形象时,您多次到广东采风调研,能否分享您在广东的经历和感受?
张翎:为《金山》我曾几次到广东采风,说起来也是十五六年之前的事了。即便在那时,我就发现广东人是最具有“国际范”的人群,倒不是因为他们穿着和谈吐的时髦,而体现在他们对待人际关系边际的态度上。
广东人宽容务实,在工作就事论事、不过于情绪化、不讲大道理。在大变化来临时,有一种超然事外的镇静,“饭照吃舞照跳”。在我来看,这是一种参透世事的人生大智慧。
文字访谈 | 记者 梁善茵
视频文案 | 记者 周欣怡
图、视频拍摄 | 记者 梁喻 曾育文 刘畅 潘俊华 宋金峪
视频剪辑、包装 | 记者 麦宇恒 余梓涛
总策划:任天阳
总统筹:林海利
总执行:胡泉 陈桥生
统筹:邓琼 吴小攀
执行统筹:朱绍杰 孙磊
-
【名家·李敬一】汉赋:洋洋大观一代之文学
2024-11-22 09:16:00 -
【名家·张春晓 杨润莲】广府文化传承中的木鱼书
2024-11-22 09:15:59 -
【名家·曹林】曹林:培养“迟钝感”,少看畅销书
2024-11-22 10:00:00 -
【名家·张翎】张翎:现实是虚构的基础,虚构就是“构而不虚”
2024-11-20 10:19:0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