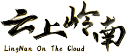

2024花地文学榜盛典特刊④
11月9日-10日,2024花地文学榜年度盛典先后在广州、深圳举行。陈平原《有声的中国——演说的魅力及其可能性》(商务印书馆2023年4月)获评年度文学评论,特发表其致敬辞、感言、专访——
【致敬辞】
陈平原不满足于传统的研究路径,时时勇于探索新领域、新方法。在新的媒介生态环境下,他聚焦“声音”这一被忽略的元素,以严谨的史家意识和文学笔法,诠释了演说在塑造社会、传承文化以及推动历史进程中的重要作用。
“有声的中国”反鲁迅的“无声的中国”其意而用之,兼及阅读、倾听与观看三种触摸历史的路径,在呈现出一个有声有色、有动有静的现代中国的同时,提示当下人:演说是“触摸历史”的又一绝佳入口。

【感言】
声音和文字二者之间的冲撞与张力在今天更加清晰
陈平原
我是广东潮州人,四十年前我在中山大学中文系研究生毕业,到北京去念博士以后就在北京工作,一待四十年。四十年后我借花地文学榜荣归故里。而且今年是中大一百周年庆典,我用我们花地文学榜这份荣誉,为我的母校献礼。
其实40年间我获了很多奖,但基本上没获过文学相关的,某种意义上我的工作更接近于历史学。我认为作为学者,能够在有一天以他们的著作获得文学界的认可,是一件值得骄傲的事。
我们知道晚清以前中国读书人主要靠写作靠文字获取功名,而20世纪以后演说传入,导致读书人在公共场合表达自己的政治见解、文化立场、生活感受的能力得到迅速加强。
某种意义上20世纪的中国,是“文字”的中国向“声音”的中国转化的一个重要时期。在这个意义上为什么我要关注演说?因为声音和文字二者之间的冲撞与张力,不仅是20世纪,在今天也更加明显地呈现在我们面前。花地文学榜评委会对我这部作品的肯定,其实是朦朦胧胧感觉到文学未来可能发生的变化以及可能的路径。谢谢评委会,更感谢我的家乡。
(文字整理:记者 何文涛)

【访谈】
1、“声音”是现代中国狂飙突进的一个重要侧影
羊城晚报:从鲁迅《无声的中国》到您这部《有声的中国》,鲁迅的这部作品对您该书的创作产生了怎样的启发?
陈平原:《有声的中国》这个书名,明眼人一看,都知道是从鲁迅《无声的中国》衍生出来的。1927年,鲁迅在香港演说时说到十年前的文学革命,用了一个比喻,那便是“有声的中国”与“无声的中国”的对决。这里的“有声”,既是写实,也是象征,比如“人是有的,没有声音,寂寞得很”。
我借用过来,辨析现代中国的“声音”与启蒙话语、政治宣传、社会动员、文学教育、学术普及乃至文章风格的演进等错综复杂的关系。表面上谈的是演说的立意、文体、姿态、身段、听众、效果等,但牵涉面很广,可以说是现代中国狂飙突进的一个重要侧影。
羊城晚报:本书中您特意兼及图像与文字,两者在行文之间相互配合,让读者尽可能“回到现场”,对您来说这是对以往历史研究方法怎样的一种反省和突破?在本书大量的图像选取背后又有着怎样的逻辑和思考?
陈平原:在几年前刊行的《左图右史与西学东渐》中,我特别关注图像与文字之间的巨大张力,而在《有声的中国》中,虽然讨论的是演说的魅力及可能性,但作为一种阐释与呈现的策略,同样兼及图像与文字。
我做的这几块,其实有某些相关性,比如文学与大学相得益彰,画报乃都市生活及文化的产物,图像与声音可以互相呈现,还有演说兴起促成了现代中国文章风格的变迁等。这也是我一直努力探索的,人文学者不该画地为牢,只要论题需要,可以尝试打破各研究领域之间的界限,把不同学科、不同媒介的研究勾连起来,一环扣一环地往前推进,说不定会有意料不到的收获。
羊城晚报:每个时代的讲演都因媒介环境的变化发生着巨大变迁,在如今媒介环境下讲演可能会有怎样新的魅力及可能性?
陈平原:1899年,梁启超接受日本人犬养毅的建议,将学校、报章、演说定义为“传播文明三利器”;而且,基于对中国社会状况的了解,梁启超认定“国民识字少者,当利用演说”。那时的中国,教育落后,识字率低,报章发行量有限,以声音为媒介进行启蒙就显得尤其重要。
今天情况大不一样,可我依旧认为,作为一种技术及文化的“演说”,依旧有能力深刻影响中国政治、思想及社会进程。只是时代毕竟不同了,当下听众的趣味及期待,牵引着演说者更多地往娱乐及教育、而不是政治或思想的方向发展。
这背后,主要是时代风云,而不是个人能力。俗话说,“时势造英雄”,是否出现或成为“伟大的演说家”,主要不取决于技术手段或能力培养。
羊城晚报:在新媒介环境下演说存在怎样的困境和隐忧?对文章的写作又会产生怎样的影响?
陈平原:三十多年前,我撰写博士论文时,关注中国小说从说书场的“倾听”转为书斋里的“阅读”,这一虚拟的声音传播向文字传播的转移,促成了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最近20年,为了研究近现代中国的思想、文化和文学,我努力捕捉那些有可能穿透历史迷雾的“声音”——尤其是晚清以降迅速崛起的“演说”。
早年“声音”保存困难,传播不易,加上“文字寿于金石”的传统信仰,我们通常更重视白纸黑字的“文章”,而不是漂浮在空中的“演说”。重建晚清以降的“声音现场”,让后来者理解那个曾经存在并发挥巨大作用的“有声的中国”,这需要专家与读者的通力合作,才有可能“幻想成真”。
如今大不一样了,声音的保存及传播变得轻而易举,只要你愿意,一部手机就能搞定一切。可也正因为太方便了,大家都不怎么把“说话”当回事(相声及脱口秀除外),缺乏认真经营的愿望以及精雕细刻的动力。长此以往,反而不太可能催生“伟大的演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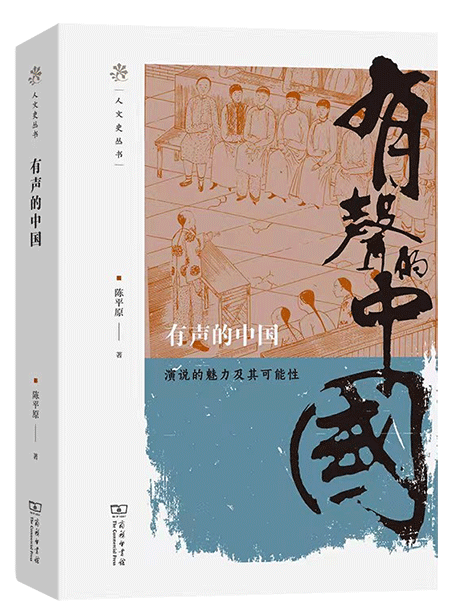
2、只要方向正确,不愁没有后来者
羊城晚报:您在自己相对熟悉的文学史和学术史之外,尝试引入大学、都市、图像与声音。在2012年发表的《“现代中国研究”的四重视野》中,您坦言对于借辨析声音来深描或阐释现代中国,在当时仍处于起步阶段。随着最新这本《有声的中国》的出版,您认为自己在这方面的探索和研究如今又到了怎样的一个阶段?
陈平原:十二年前谈现代中国研究的“四重视野”,一半在做总结,一半则是预言。那个时候,大学、都市、图像、声音这四个话题我都在展开,有的已经成型,有的尚待完善。到今天,每个话题至少有一两种拿得出手的著作,也算是初具规模,可以给学界做一个交代。遗憾的是,因精力分散,无法专精。以后的工作目标,兼及拓展与深描,力图把若干“奇思妙想”转化为坚实的学术成果。
就以“声音研究”为例,我依托北大现代中国人文研究所与河南大学近现代中国研究院,轮流召开“有声的中国”系列工作坊,希望吸引更多年轻有为的学者,共同推进这个有趣的学术话题。个人能力有限,最多只是起个头;但只要方向正确,不愁没有后来者。
羊城晚报:作为中文系教授,从创作历程和涉猎的研究领域来看,您是否更偏好于大文化研究?
陈平原:我的本行是文学史研究,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延伸到学术史探索,新世纪更有所谓“现代中国研究的四重视野”。在这个意义上,你说我更多关注“大文化”,我认可。不过,我在《有声的中国》的序言中提及,每迈出一步,都植根于原先的文学史研究,而不是完全离开,另辟新天地。
我一直认为,学者在从事跨学科研究时,必须谨慎从事,尤其进入新领域,最好和自家先前的学术兴趣有关联,那样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的长项。而且,说不好听,也是为了藏拙。
羊城晚报:在书的最后您提到最大愿望就是“在某些程度上复原那一去不复返的‘演说现场’”,您觉得这一愿望目前是否达成?
陈平原:将近20年前,我曾主编《现代学者演说现场》丛书,2006年由山东文艺出版社推出,效果不错。原计划出八卷,因“鲁迅”与“胡适”两卷在学界已有相关成果,中途搁置了,真正完成的是梁启超、蔡元培、章太炎、陶行知、闻一多、朱自清等六卷。当初约定,探究的重点不是演说文本,而是这些演说的时间、地点、环境、受众、传播、影响等。
也就是说,借钩稽每一场演说的前世今生,描摹现场氛围,追踪来龙去脉,还原特定的历史语境,让那些早已消失在历史深处的演说,重新焕发生机,甚至介入当代人的精神生活。我当然明白,由这些“纸上的声音”来复原历史上曾经存在乃至发挥巨大作用的“演说”,其实是有点冒险的。
这就要说到学者的训练、能力与职责。首先是旁搜博采,而后是精审考辨,最后还必须驰骋想象。无法板上钉钉,但尽可能做到合情合理。
羊城晚报:作为从八十年代成长起来的学者,您认为这一代学者身上有哪些共同的特质?相较于年轻学者,又存在怎样的优势与劣势?
陈平原:我们这一代学者,普遍状态是基础差但机遇好,因恰逢改革开放春风。纵观人类历史,“怀才不遇”是常态。而我们中的不少人,自身才华得到比较充分的发挥,这很难得。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是时代的幸运儿。
如果一定要总结经验,那便是我们学术成长的时代,规矩不严,风气开放,养成这一代人学术上的野心与野性。比如我自己,从思想解放、理想主义以及追求范式革新的20世纪80年代走过来,多少带有那个时代的影子。
这些年不断探索、思考现代中国研究的各种可能性。这么做,有好也有坏,最明显的便是想法多而成绩小。但作为探路者,哪怕最后证明此路不通,也可以插几个或指引或回避的路标。
3、我随时随地都在阅读思考和写作
羊城晚报:研究、评论与写作,在您生活中各占比例多少?退休后有何计划?
陈平原:人文学者工作有其特殊性,主要任务是在书斋里阅读、思考与写作。你问这三者各占多大比例,我很难回答。每个人的工作习惯不同,我随时随地都在阅读、思考与写作,三者犬牙交错,纠缠不清,无法截然分开。
另外,人文学者主要靠个人的大脑,在岗时不需要那么多经费,退休后照样出成果。北大中文系的钱理群、洪子诚等教授,退休后成果很多,也很精彩,我得向他们学习。
羊城晚报:关于学者的风格类型,我们常有刺猬型学者和狐狸型学者之分,“狐狸观天下之事,刺猬以一事观天下”,纵览您的学术历程和创作历程,您认为自己属于哪一类学者?
陈平原:如果一定要分,我只能算狐狸型了,因我的学术兴趣比较广泛,多年来上下求索,南北征战。但所有的类型划分,其实都是理想型的,处于两个极端的并不多,大多数人都像我一样,只能说偏向于狐狸型或刺猬型。
羊城晚报:2021年您受聘暨南大学潮州文化研究院院长,这些年来也陆续为古城潮州写了许多作品,是否随着年龄增长,逐渐考虑想要“落叶归根”,回归广东生活?
陈平原:出任暨大潮州文化研究院院长有其特殊因缘,具体我就不说了。这三年做了不少事情,包括邀请二十位同人合力编纂十卷本《潮学集成》;在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中专门设立“潮州文化研究专项”;借助“潮学终身成就奖”和“潮学优秀成果奖”的评审,在表彰先进的同时,有效地沟通学界与大众等。
但应该说明,我虽积极参与其事,但日常事务是暨大负责。这些年,我不断回广东,兼及学问、乡谊与亲情。但暂时没有回老家生活的打算,虽然这里的气候和饮食更适合我,但妻子是北京人,必须考虑她的因素。
羊城晚报:研究潮州文化,除了感情因素以外,对您而言还有何特别意义?
陈平原:我之所以研究潮州文化,当然有个人感情因素在里面,但并不局限于此。我多次谈及文化多样性对群体以及个体的意义。
我很庆幸自己的学问及生活有不只一个支点,国内与国外、南方与北方、大城与小城、都市与乡村,这些不同支点交叉映照,使得自己思考问题时,不会永远一根筋。有不同的参照系,促使你洞悉当下以及自身的局限性,起码看问题比较通达。
文字访谈|记者 何文涛 吴小攀
视频文案|记者 何文涛
图、视频拍摄|记者 梁喻 刘畅
视频剪辑、包装|记者 麦宇恒 余梓涛
【2024花地文学榜】
2013年羊城晚报正式创设花地文学榜,一年一度对中国当代文坛创作进行梳理和总结,也为广大读者提供最具含金量的年度专业书单。
新的十年,我们再启新征程。11月6日-11日,2024花地文学榜系列活动在广州、深圳举办。文学与时代同行,让我们从花地出发,在湾区相遇,与世界汇流。
总策划:任天阳
总统筹:林海利
总执行:胡泉 陈桥生
统筹:邓琼 吴小攀
执行统筹:朱绍杰 孙磊
-
好未来CTO田密:十年内AI会让教育颠覆性变化
2024-11-14 10:11:05 -
教育部专家熊璋:学生变化是检验AI+教育的唯一标准
2024-11-14 10:11:05 -
拜耳健康消费品中国区总经理何勇:消费市场迭代加速推进
2024-11-13 12:52:27 -
当算法跨界六弦琴:他让智能吉他成音乐演奏"新势力"
2024-11-13 12:41:4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