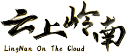
最近,作家阎晶明推出新作《同怀 鲁迅与中国共产党人》(以下简称《同怀》),讲述鲁迅与陈独秀、李大钊、周恩来、瞿秋白、陈赓、方志敏、毛泽东等中国共产党人交往或“神交”的故事,考辨史实,独抒己见,重新引发人们对近些年来鲁迅研究中被有意无意忽视的一个领域的关注。
近日,阎晶明接受羊城晚报记者专访,指出鲁迅对于当下作家和年轻人仍具有特别意义——

1、还有哪些“说”的空间?
羊城晚报:您在《同怀》一书的序言中认为,鲁迅研究有很多可以“从头说”或“接着说”的话题。在相关文献史料已基本穷尽的情况下,鲁迅研究还有哪些“说”的空间?
阎晶明:我新近完成了一篇文章,标题叫作《未必实施的写作计划——我的鲁迅研究畅想》。文章罗列了近十种个人认为可以做而且有意义的鲁迅研究选题。比如,讲鲁迅故事,是以往鲁迅传记里没有的,但是从回忆录、书信、日记里可以梳理出来的,看上去故事性不强却耐人寻味。
更重要的,这些故事可以见出鲁迅性格、性情,体现他温暖为人的一面。再比如,以年为考察对象,聚焦鲁迅在特定时期的心境、创作及社会活动。
关于鲁迅的言说是无穷尽的。有些话题是某一研究者首先提出,程度不同地引起讨论的,这就是“从头说”。但所谓从头说,也是在“接着说”的基础上部分地、局部地提出的。如果有人发现了全新的史料,甚至发现了鲁迅的佚文、信函,哪怕片言只语,那也是动静很大的事。
但我们知道,发展至今天,再想在史料上获得新发现,而且能得到普遍认可,就像到《鲁迅全集》里找出一个错别字一样,太难了。
羊城晚报:“从头说”是不是意味着之前的某些言说需要推翻重来?
阎晶明:“从头说”是一种个人意愿,不是推翻重来,而是在接续中试图表达出独特东西。让人绝望的情形是,你以为自己有什么不得了的新发现新观点,待到用文字表达出来,形成一篇完整的文章尤其是论文时,就会发现,不过大多是重复别人所说的而已。关于鲁迅,想要说出一点新的东西太难了。但是人们又忍不住要说。那是因为,对鲁迅的阅读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响:个人的成长经历,不同年龄阶段会有不同的体悟;社会思潮的影响,不同的时代背景和学术话语,都会影响对鲁迅阅读的认识与思考。
羊城晚报:照您看来,关于鲁迅,应该怎么“说”?
阎晶明:我不能说大家应该怎么说,我只能说,我自己愿意怎样说。
简单地说,我希望讲鲁迅故事,但不能编造“鲁迅故事”;我希望写出有温度、有呼吸的鲁迅,但不能是刻意的主观煽情;我希望能对鲁迅思想和作品有所阐释,但不能是板着面孔的理论空转,也不能是为凑字数的人云亦云,要坚持以学术的严谨的态度进入,又尽可能以平实的语言、有温度的表达,描画出一个自己心目中的鲁迅,并希望这样的形象能够为更多的读者认知、认可。
鲁迅的人生中有很多可以言说的话题,但不管是哪一方面的,都应与他伟大的一面相联系,或寻找、阐释其中的必然关联,才会有意义、有价值。
2、鲁迅研究历经好几回“翻转”
羊城晚报:为什么您会想起写这样一本书?
阎晶明:那是大约三年前的事了,当时我正在读9卷本的《毛泽东年谱》。阅读中所做的工作,就是将其中涉及文学的故事、话语摘录出来。我发现,毛泽东太能谈鲁迅了,仅此就是一篇大文章。同时我那时又开始关注方志敏狱中文稿传送问题,而这又涉及鲁迅。为什么不能成一个系列话题呢?
从大的角度而言,我以为鲁迅研究历经了好几回“翻转”。在上世纪80年代以后,将鲁迅从某种被神化的境地中“解放”出来,让鲁迅形象更鲜活、更生动地出现在接受者面前,让鲁迅作品得到更多文学专业的阐释,就是一个大的趋势。
但它的另一个方面是,鲁迅与政治的关系,鲁迅与政治家的关系,鲁迅社会实践中的政治色彩,在不应被夸大的同时,是不是就可以淡化?我以为这是一个很有必要重提的话题。
羊城晚报:就鲁迅与中国共产党人关系的主题而言,《同怀》一书的新意或新发现有哪些?
阎晶明:如果说这本书有什么新意,那就是重提这一话题。从我个人阅读、观察和思考来看,鲁迅与几位重要人物的交往,多以“神交”为主。但现实往来的多少或有无,并不影响我们探讨另一个更重大的问题,即鲁迅和这些人物在很多方面的相通与相知,相同与差异。
如果说交往上是以“神交”为主的话,精神上的联系用“同怀”概括也应当是成立的,是总体特征。这样的论述和强调,我以为是有意义的。
羊城晚报:关于鲁迅的研究或写作,与对其他作家的研究、写作比较,有何不同?
阎晶明:鲁迅是诞生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当中的一个名字,他代表了一个时代的文学高度,同时也开启了真正意义上的中国现代文学,不同是显而易见的。从鲁迅的名字及其作品诞生起,鲁迅研究也就随之产生了。
《狂人日记》发表于106年前,鲁迅研究的历史至今也应该有100年了。在这一百年里,产生过多少研究的成果,出现过多少不同的鲁迅观,难以细数。任何一个关于鲁迅的话题,如果没有其他的研究成果作为背景,就很难称得上是真正的研究,如果过度引用,甚至掉入到已有的研究成果里,那研究的独特性、必要性、个性就很难体现了。这就是特殊的难度。
当然还有其他的很多因素,包括鲁迅的生平以及我们对这些生平历来就存在的不同看法,甚至有的依然是谜团,它们又关涉鲁迅的思想、社会活动以及他的创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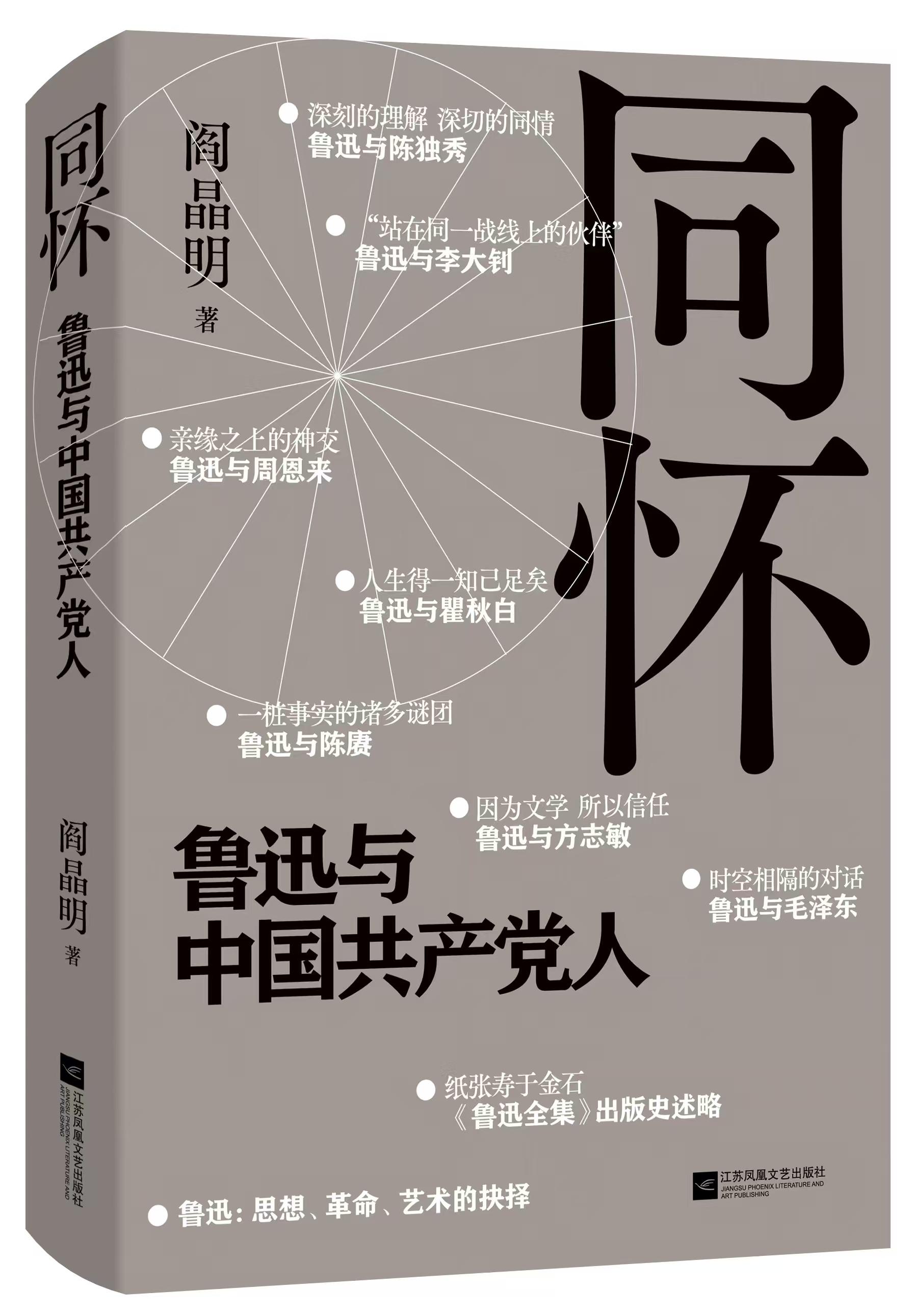
3、他仍具有“神”一般的作用
羊城晚报:您是怎么走上研究鲁迅道路的?
阎晶明:我在硕士研究生时候所学专业就是鲁迅与中国现代文学史,那应该就是一个起点吧。其实离所谓的研究还非常遥远,但是热爱之情肯定是奠定了基础。
我的第一篇文章就发表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上,文章的论题是关于五四小说中的母爱,其中也多处谈及鲁迅。之后的很多年,我的工作“专业”以当代文学评论为主。
近10年来,我有一种回到鲁迅的自我要求,比较集中地写了几部书,希望通过自己的阅读和写作,能为更多的社会公众了解鲁迅、认识鲁迅提供一点专业的知识和信息。
羊城晚报:鲁迅其人其作对您有何影响?
阎晶明:就我个人而言,阅读鲁迅无疑有很多方面的影响,这种影响绝不只是学术上的,也不只是文学上的。对于社会人生的很多认识,从鲁迅那里都可以得到重要的启示。甚至有很多具体的问题,可以从中找到答案。有一些难以克服的难关,也可以通过鲁迅而获得解决。
我举个小例子:十几年前有一次到台湾访问,我们一行有6位作家,到某大学里和学生搞一个讲座活动。将近200人的场合里,大约只坐了十几个人。校长似乎很不开心,言辞中还有批评组织者的语气。宾主难免都有一点尴尬。
轮到我讲的时候,我就讲述了鲁迅当年在北京做美育讲座活动的经历。鲁迅总共去了5次。其中一次只有一个听众,最多一次也就20人左右,甚至还有因为下雨而一个人也没有来的情形。但是,哪怕只面对一个听众,鲁迅也会认真讲述。没有听众的那次,他都在门口等了很久。这就是文化传播所应坚持的态度。
我们不是去做一呼百应的英雄,而是要坚信,只要有一个知音,就应该尽力去做好。人数少也许证明了诚意足。所以我认为,即使听众很少,但是我们一样应该认真地进行交流,而且也许还是更加有效的交流。这个故事一讲,主宾双方立刻释然。鲁迅就是如此具有“神”一般的作用。
羊城晚报:作为鲁迅的研究者或写作者,需要具备哪些基本条件?
阎晶明:说到从事鲁迅研究所应具备的条件,一言难尽。简要地说,既要阅读原著,还要了解研究的历史;既要从各种不同的观点中提出自己个人的看法,又要将这些看法放置到一个研究的“系统”里也可以成立。
当前而言,鲁迅研究队伍仍然可称庞大,人数已经不少,鲁迅的社会影响力也一样很大,很需要能够在普及鲁迅、讲述鲁迅故事、塑造真实鲁迅形象方面多做一些工作。
这件事的重要性,我认为不亚于出“重大”的研究成果。但只可惜,从事普及或讲故事,算不得“研究”,不能算“成果”,不能兑换职称之类的实际“果实”,因此即使这是普遍的、共同的认知,真正去做的依然很少。
4、对当代文学的最大启示
羊城晚报:在追新逐异的多元时代,鲁迅对于当下的文学创作、文化创造有何启发?
阎晶明:鲁迅就是我们今天文学的一部分,是中国现代文学的真正起点,也是无可替代的高峰。鲁迅对当代文学的最大启示就是,如何通过创作实践体现真正的现代性,如何处理个人和时代的关系,如何在坚持审美原则和感应时代召唤之间做出选择。
鲁迅不是一位追求“纯文学”的作家,我在书中也专门讲到了这点,他甚至经常会说自己无意于成为“文学家”。但鲁迅对小说的艺术性要求极高,甚至到了极致的程度。但是,鲁迅的另一面是,当时代需要大于个人审美趣味,需要他做出抉择的时候,他会主动呼应时代要求。
我以为,对当代作家来说,如何处理好这些关系,解决创作中遇到的难点、难题,鲁迅是一个与我们“同时代”的典范。是的,鲁迅在很大程度上并不是历史的,而是现实的。他是我们的同时代人。把鲁迅完全推向历史,有时是无意中形成的认识固化,有时也是借此可以躲避责任、使命,还可以心安理得。
羊城晚报:对于年轻人来说,鲁迅的当下意义是什么?
阎晶明:对于青年一代而言,鲁迅同样不是过去时。在网络时代,大家对鲁迅仍保持着很高的热度,这本身就是证明。
鲁迅的意义是多重的。我这里只想强调,鲁迅耐得住寂寞,并在寂寞中爆发,即使从个人事业的角度讲,也是有启示意义的。同时,鲁迅始终保持着的强烈的家国情怀,对时代社会的强烈的责任感,一样值得敬仰。他选择学医,选择从文,他不强求文学上的成就而顶着冷嘲热讽从事杂文写作,这本身就是一种责任。
因此我想说,任何时候都要怀着对时代、国家、人民的责任,不为浮躁所动,耐得住寂寞;不在乎来自自以为是者的指指点点,勇于做自己笃定要做的事,这样的鲁迅,当然值得包括青年在内的当代人学习、继承。

文|记者 吴小攀
校对|桂晴
-
彭玉平:岭南文化的传承与发展
2024-11-01 09:08:54 -
张琼:从岭南三子的岭外交游看岭南与中原诗坛的交流
2024-11-01 09:09:04 -
【名家·罗玉鑫】让岭南水墨画走向世界
2024-10-28 18:06:37 -
【名家·曾丽红】如何让名校办的新校变为“新名校”?
2024-10-28 09:10:5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