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羊城晚报全媒体记者 吴小攀
3月19日,首届暨南大学“潮学终身成就奖”“潮学优秀成果奖”颁奖仪式在暨南大学校友楼举行,来自广东省内外的60多位专家学者出席会议。自1993年饶宗颐教授倡议开展潮州学研究至今三十年间,潮学研究取得哪些进展?作为地方史研究的潮学在区域学术研究中有何特殊意义?就相关话题,羊城晚报广角版特摘发北大陈平原教授、中大陈春声教授的现场发言,并采访了“潮学优秀成果奖”一等奖获得者、《潮剧史》作者之一吴国钦教授——

两位古稀老人奋战三年完成心愿
羊城晚报:您什么时候开始关注潮剧?
吴国钦:因为是汕头人,家乡文化是我关注的一个重点,虽然人在广州,对潮剧的关注与研究很早就开始了。
1960年我读大学本科期间就写了对潮剧《苏六娘》的剧评,发表在香港《文汇报》上;1980年写了《姚璇秋的表演艺术》,发表在新创刊不久的《南国戏剧》杂志上。此文摆脱20世纪五六十年代观感式的剧评,从理论上较深入地探讨姚璇秋的表演艺术。以后我还陆续写了《潮剧与潮丑》《从〈柴房会〉谈戏曲的价值重建》等论文。
我读小学、初中时,家住在离汕头大同游艺场(戏园)不远的地方,每天下午4时,戏园免票开放给想看戏又无钱买票的人入场看“戏尾”。那时,中小学作业少,我常常在这个时间混入戏园看潮剧,我自己就有这方面的爱好,可以哼唱潮曲(如《袁金龙与苏三》曲)。
1959年,我的老同学、好朋友林淳钧到广东潮剧院工作后,经常把有关潮剧的各种讯息报刊给我,如潮剧院办的《声色艺》小报,每期他都寄给我。后来我在中大中文系主讲《中国戏曲史》。
羊城晚报:为什么会想到写《潮剧史》?
吴国钦:主要考虑到许多剧种都有自己的剧种史,潮剧却没有。京剧有200多年历史,《中国京剧史》煌煌200多万字;广府粤剧有180年历史,已出版有《粤剧史》;江浙的越剧历史只有120年,却出版了两部《越剧史》。潮剧历史悠久,它的历史比京剧、粤剧、越剧这三个影响巨大的剧种的历史加起来还长,却没有自己的剧种史,我与林淳钧心有不甘!一种强烈的责任心与使命感使我们有了书写《潮剧史》的冲动。
羊城晚报:您和林淳钧老师是如何分工合作的?
吴国钦:依据我们两人各自的特长与优势,我负责上编(1949年之前),林淳钧负责下编(1949年之后),然后互相交换审阅。写作过程中争论是不可避免的。如我提出潮剧继承南戏的艺术传统,“三小”(指小旦、小丑、小生)戏特别发达,《柴房会》《闹钗》《刺梁冀》都是;但林淳钧不同意这种提法,他说这三个戏就没有“小生”。每次争论的结果,常常淳钧胜诉,因为他对潮剧太熟悉了,我只能甘拜下风。
羊城晚报:你们写《潮剧史》有何优势与困难?
吴国钦:优势是熟悉、掌握了大量资料,写过这方面的不少论文。我一辈子治戏曲史,对广东戏曲,无论粤、潮,广东汉剧、西秦、正字、白字等剧种,都有相当的了解。林淳钧在潮剧院工作超过半个世纪,对潮剧尤其是1949年以后的潮剧很了解,他在潮剧院有“资料橱”(即资料库)之雅号。说到困难,我们两人当时(2012年)已超过70岁,精力不济,许多田野调查工作无力展开。但我们经过三年奋战,终于完成了《潮剧史》写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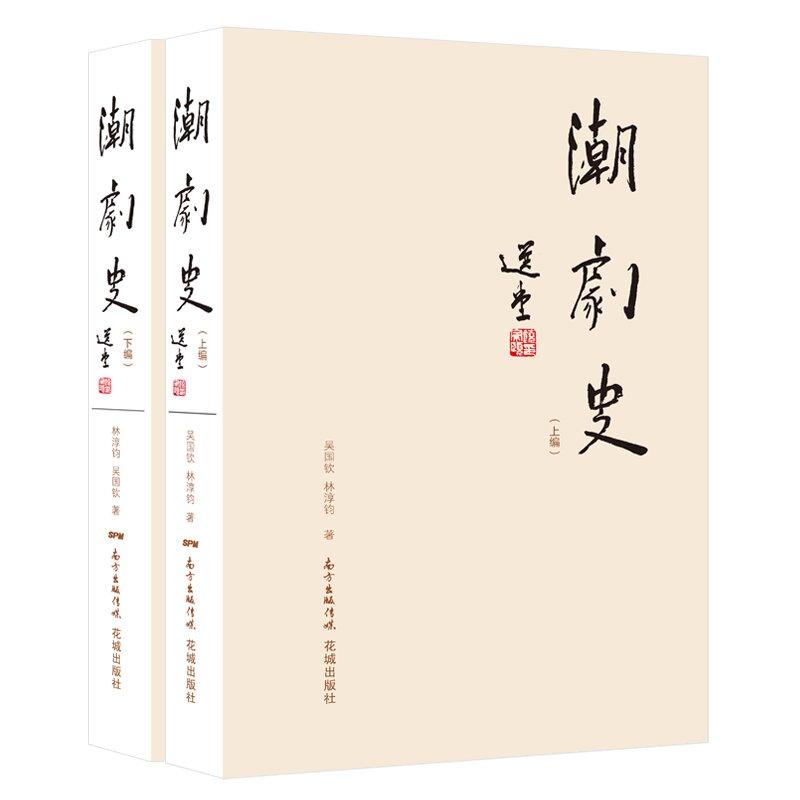
将潮剧诞生时间向前推进100多年
羊城晚报:写作过程中如何解决资料问题?如何辨识资料真伪?
吴国钦:潮剧的历史资料保存完好,尤其是《明本潮州戏文五种》(实际上是七种,在《荔镜记》与《金花女》的上栏还加刻了《颜臣》与《苏六娘》两种戏文)的发现与出版,给潮剧研究者提供了极大的方便。
研究戏曲与研究诗文不同,诗文可能有伪作、伪托,首先要去伪存真,戏曲较少这方面的问题,有的是不同版本,不同演出本的交集。因此,比较研究就成为重要的内容与方法。如大家熟知的《琵琶记》,主人公蔡伯喈在皇帝面前隐瞒了自己已婚的事实,而明本潮州戏文《蔡伯喈》则理直气壮说出“奈臣已有糟糠配”。清代潮剧还有一本《三打蔡伯喈》的戏,也是《琵琶记》所没有的。它写蔡父死前,把一根棍棒交给邻居张广才,要张广才棒打这个“生不能养,死不能葬,葬不能祭”的“三不孝”逆子蔡伯喈。这出戏的“戏肉”,是张广才严厉谴责蔡伯喈“抛亲不养,贪享荣华,为臣不忠,为子不孝,为夫不义”的狗彘不如的丑恶行止。最后,在赵五娘、牛小姐双双跪地哀求,蔡伯喈痛哭流涕忏悔之后,张广才将蔡父的遗书及棍棒交付蔡伯喈:“从今后见此物如同嫡亲,纵做三公待漏客(做朝臣),不孝之罪传万世。”可见潮剧古本与“南戏之祖”《琵琶记》有许多不同。
羊城晚报:现在看来,您认为《潮剧史》最重要的贡献是什么?
吴国钦:最重要的贡献是将潮剧诞生的时间向前推进100多年。
以前学者们认为,潮剧产生于明代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因为这一年刊刻的《荔镜记》戏文,有8支曲子标明“潮腔”,说明潮剧唱腔已经形成。我们据明宣德六年(1431年)戏文写本《刘希必金钗记》推定,潮剧应产生于宣德(1426-1435年)年间。写本是据南戏《刘文龙菱花镜》改编的,主人公刘文龙字希必。写本大量运用潮州方言俗语与名物风俗,还出现“如若不去,又着三年”(如不去,又要等三年)这一类只有潮州人才理解的句子。还有“十五夜”(指元宵节)、“卄九夜”(指除夕)这种特别的只有潮州人才懂的指示词。就是说,改编者花大力气将本子“潮州化”,为的是让一个叫在胜寺的梨园戏班演出时能够吸引潮州观众。
我们可以与京剧作一参照比较:京剧产生于1790年,其实,1790年乾隆八十寿诞时有京剧吗?没有,但京剧的“母体”产生了,四大徽班入京成为京剧孕育的契机。1431年有潮剧吗?回答是肯定的,因为《刘希必金钗记》演出时,说白是用潮州话说的,只有这样,潮州观众才听得懂,才能接受。剧作末尾,还有押潮州韵的64句潮州歌册体的演唱,对剧情进行总括交代。因此,我们认为,潮剧产生于宣德年间,距今约有600年的历史
谈粤剧潮剧“消亡”为时尚早
羊城晚报:您是1957年上大学的,你们当年专业的学习目的会不会更重于“批判”?
吴国钦:我个人觉得学术应该包含批判和创新这两个方面。所谓“批判”指的是对前人成果的质疑、批评或商榷,并非简单粗暴打棍子。
1958年,那是一个“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的年代,高校掀起学术批判高潮,我跟风写了一篇《王起老师〈西厢记校注〉的资产阶级倾向应当批判》的大字报,王老师前来观看并客气地点头。其实,一个大二学生,如果不是老师有注释,怕是连《西厢记》中许多典故辞语都未弄懂,居然发现其中有“资产阶级倾向”,岂非胡闹!但当时确实怀着一股热情在做。
接着我又写了一篇《马致远杂剧试论》的简单粗暴的批判文章。即是说,我的学术研究确实受到一些大批判的负面影响。
后来我参加了王老师主编的《元人杂剧选》《中国戏曲选》三卷本的校注工作,我自己又校注并出版了《关汉卿全集》,校注需要一个个词语、一个个句子认真校读注解,这才慢慢培养了认真细致、坚持坐冷板凳的学风。
羊城晚报:潮剧前途如何?会消亡吗?
吴国钦:戏曲是旧时代重要娱乐机制,戏曲并没有随朝代的灭亡而消亡,因为它有广泛的群众基础与文化传承基因。当然,在眼下全新的媒体生态环境下,各种娱乐手段层出不穷,戏曲的娱乐“地盘”在缩小,但我认为潮剧是不会消亡的,在潮汕农村、市镇,潮剧演出频繁,票友活动相当活跃,每逢节假日,大街小巷常常弦歌不断。潮剧在海外特别是东南亚地区也广受欢迎,泰国甚至出现“泰语潮剧”的奇观。
有的剧种可能会消亡,据20世纪60年代初的统计,当时有360个剧种,眼下最新统计为348个,可见有些剧种消亡了,但潮剧、粤剧这些有广大群众参与的剧种,谈消亡为时尚早。光佛山一地,粤剧、粤曲私伙局就有四五百个,何来消亡之说?!
受王起老师的工作态度影响至深
羊城晚报:您曾是王起教授的研究生,当时他是如何给你们上课的?
吴国钦:我在1961年至1965年当了四年王起老师的研究生,专业名称颇长,叫“中国古典文学宋元明清文学史(以戏曲为主)”,这实际上也是王老师的学术专长。他除了给我们讲授《中国戏曲作品选》《明清传奇》之外,要我们按专业要求自学,自学后提出问题,他每星期用一个上午解答我们六位研究生提出的问题。王老师自己学问做得特别精细,今天我们翻阅他遗留下来的线装《元人杂剧集》,随处都是蝇头小字的眉批夹注。
王老师常带我们研究生去看戏并参加座谈会,现在我还保留有潮剧院到广州演出时,他带我看完戏后受邀到后台与林澜院长座谈的照片。江西赣剧团来广州演出上下集《西厢记》,特邀西厢学权威王起老师观看并座谈,我们研究生全程陪同。王老师对我们说,看戏与座谈,也是学习戏曲的重要门径。当时没有专车,王老师与我们一同坐14路公交车返校。这样学习,不但理论联系实际,且师生关系非常融洽。
羊城晚报:生活中的王起老师给您的印象是怎样的?
吴国钦:王老师个性乐观豁达。20世纪50年代教授评级,全中大评了两位一级教授,中文系评了五位二级教授:容庚、商承祚、詹安泰、董每戡、王起。谁知评完后有位二级教授不满意,到领导那里投诉,说王起的《西厢记》研究是“你抄我,我抄你”,不是真学问。领导颇为难。此话传到王老师那里,他非常大度,不计较,不争辩,主动降为三级。当时二级教授薪金约320元,三级270元,相差约50元,相当于助教的月薪,但王老师不计较。
我除了学术上传承老师的一些优势之外,他对我最大的影响,是工作态度的极端认真负责,一丝不苟。大约在老师86岁时,有一天我到他家,发现天热老师戴口罩在审《全元戏曲》的稿子,忙问老师是否感冒了,老师说:“不是,现在口涎失禁,直往下流,为了不沾湿稿子,只好戴上口罩,每隔一小时换一个。”我听后心中黯然,老师已到了如此高龄还在审稿子,他这位《全元戏曲》的主编,是真主编,亲力亲为,不是那种靠名气大挂名的所谓主编。这种精神,一直是鼓励我向上的动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