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羊城晚报全媒体记者 吴小攀
图/受访者提供
近些年来,有关苏东坡的书籍备受读者欢迎,苏东坡研究专家、复旦大学中文系主任朱刚继《苏轼十讲》《苏轼苏辙研究》《苏轼评传》之后,再版推出《阅读苏轼》。日前他接受羊城晚报记者独家专访——

如跟在比自己强大得多的人后面跑
羊城晚报:您是怎样走上苏轼的研究道路的?
朱刚:我攻读博士学位时,导师王水照教授是研究苏轼的专家,所以接触相关资料比较方便。不过最初我并不做苏轼的专题研究,我的博论课题是“唐宋古文运动”,其代表作家就是“唐宋八大家”,苏轼只是其中一家。
羊城晚报:如何评价苏轼在古文运动中的地位?
朱刚:传统上,我们把“古文运动”作为历史上的一个文学运动来看待,但我认为,它实际上也兼具思想史、政治史的意义。在“古文运动”开展的同时,中国社会的领导阶层正在改变其性质,从血统决定的贵族士大夫转变为考试出身的科举士大夫。我是从科举士大夫的崛起、科举士大夫文化的形成,这个角度出发,来构建自己对唐宋文学的阐释框架的,后来就发现,苏轼是这种文化的最好象征:他以读书应举起家,投入政治,成为一个党派的领袖,有能吏之称,同时注释经典、参悟佛道,形成自具特色的一家之学,且旁通医学、水利、美食、造园等诸多领域,在文艺上也非常全面,诗、词、文、书、画都达到顶尖水准。可以说,他是科举士大夫文化极盛期的一个标志。由此,我的研究兴趣逐渐集中于此。
羊城晚报:在您今年修订重版的《阅读苏轼》一书中,展示了一个怎样的苏轼?
朱刚:在这本书中,我也是以传统中国“士大夫”阶层的变迁为背景,来叙述苏轼生平的。此书初版于2011年,当时南京大学出版社组织了一套书,写“中学语文课本里的作家”,其中关于苏轼的一册,就授命于我。为了防止学生们把苏轼当现代职业作家那样去看待,我有意采取了这样的写法。如果读者想了解,什么样的人是传统社会中比较理想的士大夫,那就看看苏轼。
羊城晚报:对于您来说,关于苏轼的研究和写作,最大的困难是什么?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朱刚:苏轼的全面发展,也给研究者带来许多困难,主要就是自己的知识结构与他不同,难以全方位地追踪他在诸多领域达到的境界。整个研究过程,就好像你始终跟在一个能力比自己强大得多的人后面跑,经常望洋兴叹。不过有时候在某一点上忽然能跟他共鸣,也喜不自胜。自身有所提高,是最大的收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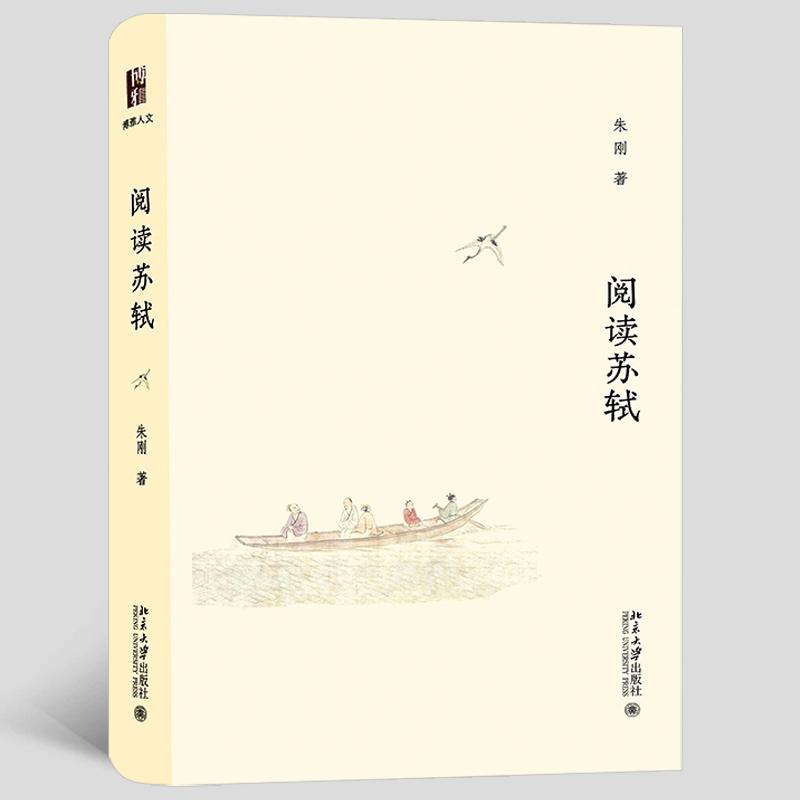
“轼有白之才,白无轼之学”
羊城晚报:有人认为苏轼是有史以来文人的集大成者,甚至超过李白、杜甫、韩愈等,如果请您为古代的文人排一个座次,大致会是怎样的?
朱刚:从文学上说,我不认为他们有高下之分,只是风格不同,读者也可以随自己的喜好去接受。从某一个体的创造性获得充分展现,贡献出的业绩的丰富性来说,苏轼为最。这一点,苏轼的领导——宋神宗皇帝也有充分的认识,当谈到李白与苏轼比较的话题时,他说:“轼有白之才,白无轼之学。”
羊城晚报:也有人认为苏轼的诗词偏“俗”了,缺乏诗格、诗味,您认为呢?这是不是崇尚理性的宋代风气有别于感性的大唐所致?
朱刚:这牵涉到宋代文学研究中非常关键的一个问题,就是“日常化”的问题。它最初由日本学者吉川幸次郎提出,用来说明宋诗的一种特点。这并不是说宋代以前的诗人就不写他们的日常生活,而是说,宋人的日常生活与此前有划时代的变化,而与今人基本相似,所以在今人的阅读感受中,宋人写出来的都比较切近世俗,他们描写的现象在实际生活中仍存在,他们的所思所感也容易理解,不像汉唐人的精神世界中有许多让我们感到陌生、惊异的东西。苏轼本人其实也感悟到这一点,他说魏晋人的“高风绝尘”已经难以复得。当然,贵族文人在文艺趣味上的那种“纯粹”性,是以贵族门阀制度为社会基础的,这种制度瓦解以后,“高风绝尘”很难复制。比如苏轼也曾企图追和陶渊明的诗歌,谓之“和陶诗”,但几乎所有读者都认为,那只是用了陶诗的韵脚,内容风格都不像陶诗,还是苏诗。

苏轼的好处是知无不言不肯沉默
羊城晚报:为什么现代人那么喜欢苏东坡(苏轼)?
朱刚:对于学者来说,苏轼的好处是喜欢表达、善于表达,他知无不言,有什么想法必须一吐为快,不肯沉默,所以无论你想探究有关他的什么问题,大致都能在他留下的文字中找到自述。早稻田大学的内山精也教授,是研究苏轼的知名学者,他有一句读苏感受,就是“苏轼决不辜负他的研究者”,你在他身上花了多少功夫,他就给你多少回报。
王水照教授写过一篇影响很大的论文,《苏轼的人生思考与文化性格》,他指出苏轼文学的一个特点,就是随时随处、终生延绵不断地反思自己的人生。由于经历复杂,这种人生思考的内容就非常丰富,而读者也容易在人生观的层面被他触动,受他影响。这大概是一般读者喜欢他的原因之一吧。
羊城晚报:其实苏东坡经历了太多坎坷了,在乌台诗案后甚至有自杀的念头,他也有低落的时候。
朱刚:从作品看,低落情绪是经常出现的。人生难免有失意者,或失意时。古往今来那么多失意的人生,寄情于文学,这才浮载起文学这艘大船,不至于沉没。苏轼的仕宦生涯,只有不到十年的顺境,大多数时间担当了异见者和逐臣的角色,所谓“一肚皮不合时宜”,虽是一句玩笑话,却也是真实的写照。但正是这样坎坷的人生,造就了一位善处逆境的东坡居士,我们从他的诗词文章中,可以看到他如何从痛苦中解脱,在各种环境中安身立命。
羊城晚报:苏东坡的人生坎坷主要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朱刚:宋代科举士大夫的人生路径,基本上就是这样:早年刻苦学习,钻研经典,了解时务,在出门应举之前,先已形成一套学说,对政治、历史、文化都有一些基本的见解,谓之“道”。考上科举后,作为官员,他们崇尚“以道事君”,按自己认为正确的道理去做,说服君主接受自己的主张,反对“苟合取容”。此后仕途或顺或逆,那就由遭遇的具体情况决定。当时司马光、王安石、苏轼,这三人可以说代表了三种政见,但三人的这种人生态度却相当一致,它具有一定的普遍性,是科举士大夫文化中最核心的部分。就苏轼本人的体会而言,“我本不违世,而世与我殊”,我希望自己有益于世,但朝廷不采纳我的意见,那就接受命运了,所谓“吾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在现代民主观念兴起之前,这是最有节操的一种生存方式了。具备这种节操的士大夫,才能创造出优秀的文化。苏轼的人生坎坷,具体地说,有时可归因于他的性格,但总体而言,是秉持操守的结果。

林语堂笔下的苏东坡偏离真实面貌
羊城晚报:后世关于苏东坡的情感生活想象是否过于理想化?
朱刚:苏轼前妻王弗,出现在《江城子》词中,继室王闰之,出现于《后赤壁赋》,还有一位侍妾朝云,见于更多诗词。我们大致可以通过这些文学作品去想象他们的爱情生活。若说妻妾以外的女性,则他的母亲程夫人,实际上是他幼年的老师。另外我还曾考证过一位“小二娘”,是大画家文同的孙女、苏辙的外孙女,幼年即到苏家,在苏家长大,后来嫁到常州,而常州就是苏轼买田安家的地方,他最后去世也在常州。苏轼对这位“小二娘”非常疼爱,可见于书信。在文学作品中写到家人、家庭生活,苏轼是比较多的,这也是“日常化”的一种表现。当然,也不宜完全用现代人对爱情的理解,去看待传统社会的男女关系,更不能用爱情在现代文学作品中的核心地位,去看待古典文学。研究唐诗的学者,经常认为唐人写“友情”比“爱情”重要,对苏轼来说,写他与苏辙的兄弟之情,也远远多于他写的夫妻之情。
羊城晚报:要正确地了解、理解一个古代文人,应该如何进入?
朱刚:就宋代以降的士大夫而言,目前专业学界比较重视对“人际网络”的考察,是传统学术中“交游考”的一种发展。比如要了解苏轼,除了苏轼本人的著作外,也要阅读他周围其他人的著作,苏辙、黄庭坚、秦观、司马光、王安石、曾巩、刘安世等,在其相互关涉、交错联结的一个“网络”中,比较客观、立体地进行把握。我所写的《阅读苏轼》的生平叙述是比较简略的,但我在叙述过程中仍想突出苏轼如何与周围的人沟通;《苏轼十讲》的篇幅比较大,涉及的同时代人物更多一些。我们国家发明印刷术最早,在北宋已迅速普及,留下大量的文集可供阅读。把同时代人的文集拼接关联起来,可以复现一段“活的时空”。
羊城晚报:您怎么评价林语堂的《苏东坡传》?
朱刚:在二十世纪的冷战语境里,林语堂把自己的政治立场、文化主张和文艺趣味,无偿“赠予”了苏轼,使苏轼如他所愿,成为一个“自由主义者”。这当然引得许多人对苏轼的好感,也扩大了苏轼的海外影响,但与一位十一世纪的中国士大夫的真实面貌,无疑是有所偏离的。
羊城晚报:现在有很多关于古代人物的传记写作出版,其中有些“戏说”是不是过头了?
朱刚:对于了解汉魏历史的人来说,《三国演义》也是“戏说”,我觉得无妨。虽然逛书店的时候,看到满架“戏说”,或夸大其词的“历史”题材书籍,确有不适之感,但想到不同的书籍拥有不同的读者,也就不十分排斥。无论如何,读书总是“贤于声色狗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