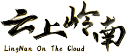

□ 郭福祥
从16世纪80年代西方钟表传入中国到1911年清朝结束,三百多年间中国逐渐形成三大钟表制作中心区域:以清宫造办处为代表的北京区域,以广州为中心的岭南区域,以南京、苏州、上海等地为中心的长江三角洲区域。广州作为中西文化交流的桥头堡,是中国最早接触和制作自鸣钟的地区,其产品与宫廷关系密切,精品进入宫廷,普通产品则销往民间。
在清宫的广钟收藏中,有一些钟表的钟体上装饰大面积色彩鲜艳、纹饰繁缛的透明珐琅,这是清宫藏广钟的重要特征。这种透明珐琅钟是清宫藏广钟中非常特殊的一类,是公认的广钟代表性作品,也是显示宫廷和民间广钟收藏具有明显区隔的品类。
要对广珐琅钟有深入的认知,广东透明珐琅的历史是必须解决的首要问题之一。经笔者近年研究,后者的历史脉络问题基本解决。笔者近期新作《广钟历史的几个关键性问题》一文,对此展开详细探讨。
所谓“透明珐琅”,是将透明釉料施于金属胎体之上,经烧制后形成一种可透视胎底,器物表面具有自然亮丽、明暗变化视觉效果的珐琅艺术作品。在中国,这种珐琅直到18世纪才有在地的制作实践,是各类珐琅中最晚传播到中国的品种。而“画珐琅”通常是指铜胎画珐琅,即在铜胎上填涂珐琅釉烧制,然后再在其上用各色珐琅釉画出纹饰低温烧制。画珐琅技艺在康熙时传入中国,受到皇帝和宫廷重视,在宫廷和广州得以大力推广,逐渐发展为宫廷艺术的重要门类。
镶饰透明珐琅是清代广钟最具代表性和标志性的装饰手法。工匠们一般根据钟表的造型将钟表外壳面分解成不同部分,每个部分单独烧制透明珐琅器物或珐琅片,然后再组合、拼接和镶嵌到钟体的相应部位。一件外壳嵌满透明珐琅的广钟,多者要烧配几十件大小不等、形态各异的构件和珐琅片。
笔者这些年来对收藏于国内各大博物馆,尤其是北京故宫博物院和台北故宫博物院的透明珐琅藏品,以及流散在世界各地的广东透明珐琅作品进行了认真细致调查,对广东透明珐琅作品制作风格及其演变有了一定认识。在这一过程中,研究的基本思路是根据胎体、技术和装饰风格对现存实物加以分组,探讨其前后递进关系,从而确立广东透明珐琅历史发展大致的时间纵向坐标。同时,探讨广东透明珐琅的不同市场及其影响,建立其空间横向坐标。
在梳理现存广东透明珐琅实物过程中,笔者首先关注到的是作为透明珐琅制作基础的胎体,材质有金胎、银胎和铜胎之别。这三种胎体似乎有个逐步递进的过程,可作为区别广东透明珐琅的第一层级要素。其次是在同一种胎体上,透明珐琅的施作技术和装饰手法又有明显阶段性演变,可作为区别广东透明珐琅的第二层级要素。
根据这两个层级要素的变化和演进关系,可将现存广东透明珐琅实物分为四组,即金胎浮雕透明珐琅、银胎浮雕透明珐琅、装饰金银片花纹的铜胎透明珐琅、透明珐琅和画珐琅相结合的铜胎珐琅。
金胎阶段作品主要是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的28件金胎浮雕透明珐琅作品。这些作品基本是根据宫廷要求,按照法国工匠所作金胎弦纹地番莲花纹内填透明珐琅碗的工艺制作。关于这件碗的情况,后面将详细讨论。这28件作品均是在金胎上錾刻出番莲花纹,花纹四周刻弦纹为地,各部分填充不同颜色的透明珐琅,可以透视胎地,色彩艳丽。器形虽根据宫廷收藏的需求有所变化,但纹饰和做法基本不变,都源自当时宫廷所藏康熙时期制作的金胎黄地番莲花卉纹画珐琅碗。除最早的一件康熙款浮雕透明珐琅金碗外,其余27件都有“乾隆年制”款识。
银胎阶段作品主要是北京故宫博物院和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的银胎浮雕透明珐琅水丞1组、长颈瓶2对、炉瓶盒1套。银胎透明珐琅存世数量极少,可能只是一种过渡性试验产品,很快便被更稳定的铜胎替代。
铜胎阶段的透明珐琅作品数量较多,主要收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和海外各博物馆。经笔者初步统计,其数量超过250件。铜胎阶段又可分前后两个时期:前期作品主要是为宫廷生产,是广东透明珐琅技艺发展最成熟和艺术水平最高的阶段,与宫廷的密切联系使得透明珐琅被广泛应用在各种宫廷器物特别是钟表上;后期则将透明珐琅和画珐琅相结合,呈现新的风格,而且这种新风格完全是为了适应海外市场而出现,产品基本销往海外,显示出广东透明珐琅市场由国内转向海外的历史性转变。这一转变使成本成为透明珐琅品质高低的决定性因素,产品品质在价格杠杆的作用下不断下滑,广东透明珐琅技艺最终归于沉寂,不知所终。
这四组透明珐琅器物基本形成了广东透明珐琅前后相续的演变序列,第一组金胎浮雕透明珐琅是这一序列中最早的产品。因此,只要我们解决了金胎透明珐琅制作的时间和技术来源问题,就解决了广东透明珐琅技艺的整体起源问题,同时也解决了广东透明珐琅钟的起始时间问题。


近年来,海峡两岸研究人员在清代宫廷珐琅研究方面取得可喜进展。王竹平透过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康熙款浮雕透明珐琅金碗所用金胎上的法国巴黎金匠行会戳记,尤其是课税标章和纯度标章,明确该碗所用金胎制作于1777年的巴黎,从而推知该碗施釉连同落款的完成时间应不早于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排除了其为康熙朝制品的可能性。通过对清宫相关档案和实物的梳理,王竹平厘清了此组28件金胎浮雕透明珐琅器制作的背景和大体脉络。其中,乾隆时期制作于法国的康熙款浮雕透明珐琅金碗是具有重要意义的作品,它很可能是清宫所有金胎浮雕透明珐琅器的创意源头。
王竹平还推测这件康熙款金碗之所以在法国制作,可能与乾隆四十年(1775年)广东粤海关执行的一项对康熙和雍正朝画珐琅器进行复制的乾隆皇帝的指令有关。据造办处“活计档”记载,乾隆四十年十一月,皇帝指令太监胡世杰将包括金胎西洋珐琅碗在内的10件康熙款和雍正款画珐琅器交给粤海关监督德魁,照样各做成一件,并指示“不要广法琅,务要洋法琅,亦要细致烧乾隆年制款”。这里的“洋法琅”到底是指广东制作的西洋风格的珐琅,还是指西洋制作的珐琅,粤海关官员可能无法做出准确判断,于是采取了比较稳妥的办法。一方面,粤海关在广东复制一份。两年以后的乾隆四十二年十一月,将照样新做成的10件“乾隆年制”款画珐琅器呈交,做样的10件画珐琅器也一并交回。另一方面,粤海关又把做样的10件画珐琅器分别画图,通过在广东的西洋商人将图样带往法国,觅工匠再做一份。
王翯在北京故宫所藏乾隆款铜胎画珐琅菊纹壶底部发现的法国著名珐琅画师Joseph Coteau(1740-1801年)的签名,证实了粤海关确实向法国发出了制作样本的要求。以此为线索,王翯又从两岸故宫博物院的收藏中辨识出与此壶一起在法国复刻的同批其他画珐琅作品(王翯:《西洋制作乾隆款画珐琅器物考》)。
据档案记录,法国制作的这批画珐琅器于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十一月由粤海关监督穆腾额送到宫廷。其后王翯还在此壶的胎体上发现了金匠、巴黎地区征税和金属纯度标章,确认壶体的金胎制作于1783年(王翯、刘瀚文、翟毅:《西洋制作乾隆款画珐琅器物考补证》),这与清宫档案记载完全相合。赵冰最近在法国文献中也发现了将这些珐琅器的样稿带往法国制作的线索(赵冰:《从乾隆皇帝1775-1776年“法国定制”看中法宫廷交流的私人性》)。中法文献和实物都证实了清宫通过广东粤海关向法国定制这批画珐琅器的事实。
在上述研究基础上,笔者首先通过此组器物中一对乾隆年制款金胎浮雕珐琅提篮的原装木盒上刻有“乾隆年制金胎广珐琅花篮一对”的款识,作出“可以很明确地知道当时宫廷认定此类金胎浮雕内填透明珐琅为广东制作,是广珐琅的一个类别。据此,我们可以将技法和风格与此一致的台北故宫博物院藏乾隆款金胎浮雕透明珐琅作品全部认定为由粤海关制作的广东透明珐琅”这样的判断。之后又根据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穆腾额将这批法国制作的画珐琅器送往宫廷时还附有“做样珐琅碗一件”的记载,及前述法国工匠1777年制作的康熙款浮雕透明珐琅金碗和1783年制作的乾隆款铜胎画珐琅菊纹壶之间时间相距6年之久的情况,推测在这批法国定制的珐琅器制作过程中,中法之间曾有过反复交流讨论,有过误解和纠偏。正是在这一过程中,法国透明珐琅技术进入中国,并为乾隆宫廷所关注。
当时可能的情形是,粤海关一面按照实物在广州当地募工制作,同时将这10件器物画样,委托法国商人将样稿带往欧洲,让法国工匠另做一套。画样很快送到法国,法国方面对此项活计高度重视,募聘巴黎著名珐琅工匠Joseph Coteau等参加制作。出于谨慎,法国方面在1777年按照接到的图样先试制了一件金胎珐琅碗运往中国,希望得到中国方面更具体的意见,以使整个工程取得双方满意的结果。不知什么原因,可能是对图样的理解有偏差,法国工匠将金碗原本应采用的“画珐琅”制作工艺误用了錾胎内填“透明珐琅”做法。这件錾胎透明珐琅金碗,也就是台北故宫博物院现藏的康熙款金胎浮雕透明珐琅碗,当时制成后被运回中国进呈乾隆皇帝。因和当初做样的康熙款画珐琅金碗完全不同,乾隆皇帝意识到西洋工匠并没有领会其意图,于是再次将原做样的画珐琅碗送到广州粤海关,让法国商人转往巴黎。通过样器,法国工匠得以领会宫廷的画珐琅制作意图。1784年,法国工匠全部完成这批画珐琅器的制作,做样珐琅碗和新做的10件画珐琅器一起回到清宫。这样就可以理解都在法国巴黎制作,为什么1777年康熙款浮雕透明珐琅金碗和1783年Coteau款铜胎画珐琅菊纹壶的制作间隔了6年之久,也就可以理解原本已经回到乾清宫的做样珐琅碗为什么又出现在后来乾隆四十九年呈进的活计之中了。
法国方面制作的金胎透明珐琅碗样品送到宫廷后,乾隆皇帝在纠正法国工匠偏差的同时,也对此碗特别的透明珐琅产生了兴趣,由此引发了后续“乾隆年制”款金胎透明珐琅器的制作。
这是清宫最早一批广东透明珐琅作品,制作时间应在清宫收到法方试制金胎透明珐琅碗的1777年之后。
至此,可以得出广东透明珐琅工艺是由法国引进的结论。引进的契机源于乾隆皇帝通过粤海关依样向西洋定制画珐琅器过程中,法国工匠偶然地偏离顾客要求,将原本应该是画珐琅的金胎碗做成了内填透明珐琅,由此引发了乾隆皇帝命粤海关仿烧的系列制作,开启了广东透明珐琅从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到晚清一百余年的发展史。
由此也可以推定,装饰透明珐琅的广钟出现的最早时间亦在1777年左右。
而广珐琅钟的下限,按常理和逻辑推断,应以广东透明珐琅历史的下限即晚清为广珐琅钟的下限。要注意的一点是,宫廷和民间的广珐琅钟在存续时间上的不同。笔者根据两组广东透明珐琅实物提供的相关信息进行推断认为,可将广东透明珐琅市场由以宫廷为主转向以海外和民间为主的时间定在19世纪20年代初期。在此之前的广东透明珐琅都是专门为宫廷生产,相应地,此一时期制作的广珐琅钟也都为宫廷所收藏;在此之后,广东透明珐琅转向民间和海外,此时期制作的广珐琅钟也被排除在宫廷收藏之外,主要面向民间。最后,随着晚清广东透明珐琅技艺的消失,广东民间装饰透明珐琅的钟表也随即销声匿迹。
综上,借助笔者和其他学者的研究成果,我们可将清宫收藏的装饰高水平透明珐琅广钟的制作时间大致界定在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至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之间。这些代表清代广钟制作最高水准的作品,实际上是在乾隆晚期至嘉庆时期不到半个世纪的时间段内生产的。广珐琅钟是一个生产时间短暂但技术登峰造极的广钟品种。
作者简介:郭福祥,故宫博物院二级研究馆员、宫廷历史部首席专家。
-
【名家·杨克 侯玉婷】白玉草
2025-01-13 23:26:01 -
【名家·侯玉婷 孙幼明】过年与贴春联
2025-01-10 21:54:46 -
广钟历史的几个关键性问题(上):木楼钟是贯穿广钟历史始终的代表性品种
2025-01-10 09:54:39 -
“吾犹昔人,非昔人也”——漫谈中国文体学研究
2025-01-10 09:54:3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