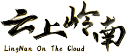

□ 祁丽岩
“岭南三大家”指清初广东诗人屈大均、陈恭尹、梁佩兰,因岭南诗人王隼于清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选刻的《岭南三大家诗选》得名,是当时岭南地区最享盛名的三位诗人。他们不仅在岭南诗歌史上占据重要地位,对岭南文化的形成和发展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古琴是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古琴所蕴含的独特文化品格与岭南三大家所追求的理想人生境界有着相似之处,加之清初岭南古琴文化日渐兴盛,古琴成为文人间雅聚交流的文化媒介。抚琴、听琴、品琴、创作琴诗和琴歌等成为岭南三大家交游的重要内容。现存的岭南三大家诗歌作品中有很多涉及古琴书写的篇目,其中屈大均近300首,梁佩兰近70首,陈恭尹近40首,古琴作为一个特有的文化符号意象,在被书写的过程中不断生成诗人的自我镜像,映射出岭南三大家在时代变局中复杂多元的精神内涵。
以琴入世,慷慨悲凉的遗民情怀
岭南三大家生活在政治风云突变的明末清初,随着清兵入关,朱明王朝倾覆,三位诗人都沦为由明入清的遗民诗人。虽然他们的境遇和选择不同,或奋起抗清,或蛰伏山林,或被迫出仕,或遁入空门,但是那种国破家亡的伤痛是共同的,相似的时代背景和生活经历成为他们情感的连接,因而三人交游甚密,经常一起雅聚唱和、抚琴品茗、相互慰藉,琴诗应运而生。
岭南三大家中,屈大均的琴诗最为高产,有数百首之多,且内容最为丰富,这和他旺盛的创作力是分不开的,也与他的家学传统相关。其父屈宜遇精医理,通经史,好饮酒,善弹琴,耳濡目染中屈大均对古琴颇为熟悉,自然入诗。他的诗中,弄琴、鸣琴、鼓琴、听琴、观琴、言琴、咏琴、咏琴台和琴囊、琴歌以及记录与琴客的交游往来等,无所不包。屈大均前半生都致力于反清运动,是岭南三大家中最执着的抗清志士,其积极入世的反抗精神和遗民情怀在他的多首琴诗中都有所体现。“挥手向遗老,知音怀古贤”(《听八十有五罗翁琴》)“发是先朝白,颜非故国红”(《罗翁八十有五善琴诗以赠之 其一》)诗中的“遗老”“故国”足以彰显其遗民情怀。再如,“我为园客丝,缠绵玉轸中。玉轸有时折,朱丝无断绝。大弦含幽兰,小弦吐白雪。鼓舞尽神明,庶以酬先哲。”(《咏梁子六莹琴》)这里,诗中之琴已是自我形象的化身,诗人宁为玉碎,玉轸可折但“朱丝无断”。“朱丝”与“朱明王朝”暗合,意指诗人之忠贞恰如“幽兰”“白雪”般高洁。最能体现屈大均遗民情怀的是《烈皇帝御琴歌》,诗中叙述崇祯皇帝所弹御琴七弦在演奏中无故自断,遂兆国变,御琴从此流落民间之事,情感沉郁激昂,“我从李卿请琴观,楚囚相对泣南冠”“余音绕梁何缠绵,满堂宾从皆涕涟。请君罢弹莫终曲,恐令南北诸侯哭。”该诗以琴事写人事,字字血泪,慷慨悲凉,其忠贞爱国的遗民情怀直透纸背。
与屈大均相比,陈恭尹、梁佩兰的琴诗数量虽少,但遗民情怀也蕴含其中。陈恭尹又因12岁丧母、16岁举家遭戮的不幸遭际,其琴诗中的遗民情怀在国破家亡的沉痛之外,更有一种身世飘零之感。“莫上高台坐,南音不惯寒”(《生生园十咏 其七 琴台》),南音的孤独悲凉,恰是自我写照。“况乃风高水波立,海隅咫尺非吾土。豹之斑,下人间,鳄之横,出深阻。掩君泪,为君吟。彼琴者木木有心,四海男儿何至今。”(《崇祯皇帝御琴歌》)同样写御琴,同样是慷慨悲凉,与屈大均不同的是,陈恭尹因感怀身世与琴共鸣进一步生发出“木木有心”的感慨,人琴相通,物我两化。而梁佩兰作为岭南三大家中唯一仕清的诗人,其琴诗中的遗民情怀显得含蓄委婉。“十年躁气此尽平,今夕始闻君子声”(《听唐山人弹琴》)“天下和平不能外,古调于今少人爱”(《容栎堂鼓琴歌》)等琴诗中皆不见激越悲愤之气,加之梁佩兰又是三人中最精于古琴、痴迷于古琴的琴人,心性超然,使得其琴诗中更有一种不问兴亡的平和淡然。然而,诗中虽不直问兴亡,却仍能看出其对乱局的厌恶与排斥,对“天下和平”的期盼与热爱,骨子里仍是缠绕不去的遗民情结。
琴为心镜,诗为心像。细读岭南三大家的琴诗,可以观照出他们以琴入世、感物思国,借他物言说自我的精神内涵。
以琴避世,无可奈何的逃禅隐逸
在政权动荡、风雨飘摇的明末清初,虽有屈大均等一大批志士仁人奋力抗清,但仍阻挡不了国破家亡的历史命运。1650年,清兵攻陷广州。这一时期许多曾经参与过抗清的仁人志士纷纷逃往寺庙丛林,参禅礼佛,以逃避斧钺之祸。据史料记载,屈大均和梁佩兰都曾出家为僧,尤其是屈大均,20岁出家,33岁还俗,有长达十余年的参禅经历。虽然他们的初衷是避祸,但是长期的佛门生活不能不在他们的思想上形成烙印,产生影响,他们的诗作也不可避免地蕴含佛理、富有禅意,又因古琴本身就与禅宗有着天然的亲近,使得他们的禅佛思想在琴诗中表现得更为明显。
屈大均的《弄琴有怀石斋翁》有“泠然林木外,太古有余音”“心外无山水,高深只自知”等句,“林木外”的清净,“心外无山水”的明心见性,皆富有禅意,与禅宗悟道的境界类似,可以看出屈大均虽然在出家期间仍从事反清活动,但受禅宗影响,内心不知不觉浸染了逃禅出世的思想,自然生发一种对林泉隐逸生活的向往,这种归隐意识在晚年更加明显,屈大均晚年有很多与琴客交游往来的诗作。“独坐偏宜夜,秋光是客心。如何明月影,只爱白云林。”(《秋夕与琴客作》)“长啸和君琴,风吹山水心。”(《送琴客詹大生丈》)从中可以看出最富有反抗精神的抗清志士屈大均也在政治风云尘埃落定之后在精神上无奈归隐、心向山林。
“梁六莹初亦为僧,不久而归举解元。”(檀萃《楚庭稗珠录》)梁佩兰出家的时间较短,但却是岭南三大家中最有佛性的。他随遇而安,易代之际,始终有一种“识时务”的独醒,因此也是三人中唯一仕清的。他自年轻起便常与僧人交游,访僧悟道,晚年更自称二楞居士,一心向佛,以弹琴、品琴、藏琴为乐。他的《容栎堂鼓琴歌》中有“何时山无车轮路无马,官府民间两闲暇。老夫对客日微吟,饱饭弹琴栎树下。”字里行间彰显其摒弃世俗的出世之心。又《听周冷泉弹琴 其一》中有“何事充吾耳,湖钟又到林”,其隐逸之心,一语道破。再到“忘形有余照,寂感成空音。谁与师蝴蝶,同将物化寻”(《后十九秋诗 其十 秋琴》),诗中禅意幽幽,超然物外,已类佛家语。
身负国仇家恨、命运最为悲惨的陈恭尹,恢复故国是他一生的志向,但晚年也在复国无望的悲苦中逐渐消磨了斗志,接受现实,“身隐新朝”(陈恭尹《独漉堂集》)。其琴诗也成为他的思想历程和精神演变的见证,从“木木有心”“南音不惯寒”的嗟叹悲愤,逐渐转为“一卷慵开独坐吟,不冠不袜坐松阴。天涯何患无知者,流水高山共此心”(《题静像善琴》)的平和恬淡,进而再到“幽人何所有,虚室有清弦。素手偶为抚,秋心一渺然”(《弹琴》)的空灵清幽,折射出陈恭尹由入世到出世的精神轨迹,在琴道与诗道的共同疗愈下,陈恭尹饱经血雨腥风摧残的内心终于走向平静。
岭南三大家的琴诗,意在琴外,琴在世外。他们各有遭际却殊途同归,以琴避世、逃禅隐逸,是他们在政治风云席卷下的无可奈何的必然选择。
以琴修身,觉知生命的自我圆融
古琴作为一种古老的乐器,蕴含着独特的审美品性与文化内涵。嵇康认为“众器之中,琴德最优”(嵇康《琴赋》),并因此建构了“含至德之和平”的琴德论。这种琴学思想对后世的文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琴德之德在传统文化中逐渐与君子之德建立密切的关联,琴成为文人“修身理性,反其天真”(蔡邕《琴操》)的道器。岭南三大家皆出身书香世家,深受儒家传统文化的影响,同时又生活在明末清初岭南古琴文化勃兴的大环境下,因而以琴修身便成为他们历经政治风云跌宕后修心养性完善自我人格的路径,这在他们的琴诗中多有印证。
屈大均的《罗翁八十有五善琴诗以赠之》中有“老知琴德好,新斫峄阳桐”“蠲愁花有力,养寿酒无功。为我弹神化,泠泠松下风。”等句,直言琴德之好,可见其早已将琴视为修身之器。同时诗中他还将琴德具体化,“养寿酒无功”,功在“泠泠”之琴也,弹琴令人心旷神怡,抚上一曲便可以“挥弦作神仙”了(《听憨上人弹琴》)。陈恭尹晚年高隐羊城之南,同样钟情于琴。“幽人何所有,虚室有清弦。”(《弹琴》)“众窍因成籁,一弦犹抚琴。岂能谐里耳,聊以散幽襟。”(《羊城月夜同王紫诠吴山带次蓝公漪韵》)从中可以看出琴既是他幽居的陪伴,也是他孤高气节的象征。梁佩兰精于操琴,三人中与古琴最为亲近。他在《赠汪苕文民部》中把琴视为大雅,并作为他孜孜以求的人生境界:“提琴拊弦按宫徵,不向大雅当谁寻”。甚至在《听唐山人弹琴》中他直接将琴声比作“君子声”并予以歌颂,在某种程度上,琴已成为他安身立命的精神寓所。
在明末清初的历史境遇中,岭南三大家尽管人生选择和生命历程各有不同,但不约而同在晚年都选择了“含至德之和平”的古琴作为修身之器,琴德与诗心相融,琴境与禅境相通,他们的心境逐渐趋向平和。无论是复明大计理想幻灭的屈大均,还是国破家亡报仇无望的陈恭尹,抑或是怀才不遇报国无门的梁佩兰,都逐渐化解了内在的冲突与矛盾,并积极与仕清的文人和达官贵人交游往来,诗中的古琴书写也从最初“御琴”诗的悲凉激愤转为冲淡平和、空灵娴静,他们生命态度的转变是痛定之后对自我的超越,以此抵达生命的圆融境界。
岭南三大家笔下的古琴书写,是诗人在特定历史时期建构的人琴互文的自我形象表达。以琴为媒介可以洞察他们幽深隐蔽的精神世界,从对抗到逃离再到平心静气,表现出他们非同寻常的生命张力。世事沧桑巨变,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而岭南三大家以艰苦卓绝的生命意识,在入世与出世的交融碰撞中,在琴心与诗心的相互作用下,不断修行,最终与自我和解。
(作者是广东技术师范大学文学与传媒学院副教授)
注:本文是2021年度广东省社科基金岭南文化专项“异质同构:岭南古琴文化与岭南诗学传统之关系研究” (GD21LN07)的阶段性成果
-
【名家·黄天骥】戏曲精研承薪火 融会贯通拓新天
2024-12-07 12:32:12 -
何以“天时、地利、人和”——广东南路人民支援海南岛战役的启示和意义
2024-12-06 08:35:25 -
抗美援朝期间广东社会各界志愿赴朝事迹考述
2024-12-06 08:35:24 -
【名家·郑义富】中小学课程改革需警惕:狭隘科学主义、学科专业主义、盲崇技术理性
2024-12-04 14:20:3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