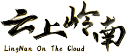
《我的大哥几个姓(下篇)》
作者:陶斯亮 朗读:侯玉婷
导语:原国务院副总理陶铸与曾志的女儿陶斯亮,用她朴实无华的文字撰写了《我的大哥几个姓》这篇文章,真挚而感人。在文中,她分享了许多鲜为人知、扣人心弦的故事,展现了她深厚的人文情怀。受到社会广泛尊重的公益人士陶斯亮,大家亲切地称她为“亮亮姐姐”,她希望我能朗读这篇文章。我欣然答应,非常荣幸能与大家共同分享这篇充满情感与智慧的作品。

艰难选择
1964年社教运动中,大哥犯了一点小错,跑到广州避难,这次他请求母亲让他留下。“但是,曾志却拒绝了儿子。什么原因?难以定论!”我的年轻作家朋友李春雷在他近期发表的《真有后来人》一文中这样写道。母亲为什么拒绝大哥?我认为这个问题是有解的。
大凡经历过的人都知道,1964年是一个特别的岁月,那是一场大灾难的尾声,又是一场更大灾难的前夜。做为生产队记账员的大哥被查出有错,并正在审查中。极“左”的四清运动无限上纲上线,大哥私来广州恐铸成大错,母亲把大哥留下来在当年既有失公正,也违背原则。再说,大哥时年36岁又是文盲,在风声鹤唳的环境中,更是难以安排。
简言之,这是老一辈革命者在自律与亲情的纠缠中做出的艰难选择。
再次相聚
待后来母子又相见,中间相隔20年。直到1984年,母亲以74岁高龄从中组部退休,又燃起她对亲情的渴望,于是召唤她的孩子了。
我第一次见大哥是1985年,当年井冈山既没有高速公路也没有机场和火车,大哥带着两个侄子路途迢迢,千辛万苦来到北京,这一趟总得走个三四天吧!
母亲这边也是很兴奋,破例让吴秘书和司机小邢去火车站接他们。平时母亲是不准家人搭乘她的专车的。
终于见到了大哥!他个不高,清瘦,不同于我和二哥的泡泡眼儿,他眼睛深邃,面部立体,笑容真诚。“大哥年轻时一定很英俊!”我悄悄地想。两个侄子长得也好,很清秀。大哥和两个侄子衣着虽然简朴陈旧,但并不是我想象中的庄稼汉模样。最让我感动的是,大哥竟然是挑着一副担子千山万水来看望母亲的,这份情真是太重了!一副担子两个箩筐,一个箩筐装的是井冈山的土特产,另一个箩筐装的是珍贵的石拐(石蛙),这些家伙吓我一跳!这是大哥能送给母亲最好的礼物了。现在石蛙已经被列为井冈山保护动物。
全家隆重地迎接了大哥,母亲更是高兴,一连几天陪他们去游览北京的名胜古迹,甚至不顾年迈陪儿子登上了长城。

血浓于水
后来母亲又于1987年和1993年两次上井冈山去看望大哥一家。刘朝辉秘书回忆1987年陪母亲上井冈山的情景:“曾老从一进门就握住石大哥的手,吃饭时也不曾松开,那种慈母情溢于言表。”
后来,母亲把她的二孙子草龙和曾孙女石丽接来北京。母亲为石丽联系了北京旅游学校,毕业后我带她去了广州。我向一位搞房地产的老板声情并茂地讲述了石家、蔡家以及夏家的悲壮故事,后来这位老板接受了石丽。石丽在做房产销售时认识了她的真命天子,一位家境殷实的广州小伙子,如今孩子都上大学了。妹妹蔡燕也来了广州,也嫁了个好人家。草龙的两个女儿也都在广东发展。唯有全家长子蔡军,在驻港部队完成兵役后,回到井冈山,在中组部办的干部管理学院工作,是位素质很好,很有能力的年轻人。
话扯远了,再说回大哥。自从1985年重逢后,与大哥一家就建立了亲情关系,侄子们常来常往,我在母亲去世前后更是频繁上井冈山,每次都在大哥家里吃一顿丰盛的农家菜。大哥不善言辞,但他一声妹妹的称呼,一句对妈妈的问候,就足以表达对母亲真挚的爱了。

最后告别
大哥再来北京,则是陪母亲过她最后一个生日。
我在《曾志与夏明震》一文中,描述了这个生日场面:“母亲今天有点激动,讲了不少话,她对大哥和二哥说:‘我对不住你们,让你们吃了很多苦。春华残疾了,石来发至今还是个农民劳动者。但是当时我也是没办法,我也只是个小孩子,又要行军打仗,环境很苦,没有办法养孩子,要请你们原谅!’”
刚强又倔强的母亲,在生命的最后时刻请求两个儿子的原谅,说明在她心中始终都惦念着这两个苦命的儿子。那天,二哥几次哽咽流泪,他对母亲的感情太复杂了。相较之下,大哥简单得多。他诚恳地对母亲说:“你白养我们了,你病了我们都不能来照顾你,劳累妹妹一个人了。”

我很敬重大哥,他过得清苦,他的房子破旧,他有很多的艰难,但他恭敬温厚,朴实真挚,从来没有埋怨过母亲,反而一再对我说:“我们不能照顾妈妈,全靠妹妹了,妹妹辛苦了!”他在母亲面前的从容得体,让我暗自惊讶,不愧是夏明震的骨血啊!
土地纠结
如今,大哥的故事早已冲出井冈走向全国。侄子们讲述大哥和母亲的故事中总少不了一个情节,就是母亲不为大哥一家办商品粮这件事,可能这是两个侄子一直最纠结于心的事吧。他们的讲述本是为了突出奶奶的革命性和原则性,但也有不少人感觉这有点不近人情。
其实这纠结的原因就在于两代人对土地的看法不一样。
解决孙子们的商品粮问题,对奶奶而言并不是一件难事。我也曾经问过母亲:“你一向热心助人,帮助过的人不计其数,为什么单单不帮一下自己的孙子呢?”妈妈很严肃地对我说:“我们干革命流血牺牲,不就是为了让他们能得到一块田地吗?怎么说不要就不要了呢?”
这个道理如今越来越清楚了,我曾再三对家里从农村来的阿姨说:“上面再怎么忽悠你,你都绝不能卖你的地!将来最值钱的就是土地!”
很多亲朋好友都去过我大哥家,无不艳羡赞扬我大哥家的田园风光。虽然房子破旧些,但风水特好。四周是广阔的稻田,屋前有一口池塘养着鱼和鸭。屋后是一座翠岗,长着茂密的竹子和各式树木,还有石家祖坟和我大哥的墓,不远处有一条清澈的小溪,日夜潺潺流淌。大哥家就是我心目中的美丽乡村。如今听侄子金龙(蔡接班)说,他们已经把祖宅修葺一新。守着这方好山好水,不知道侄子们现在会不会幡然醒悟,当初奶奶的决定是多么睿智啊!
说到底,侄子们的事,是改革开放后,中国城乡二元化结构,巨大的城乡差别,致使大量的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在这样的时代大背景下,我理解侄子们对城市生活的渴望,毕竟在城市能找到较好的工作机会,能挣到更多的钱,无可厚非。
亲情与命运
我的侄子蔡接班和石草龙,跟我大哥一样,一辈子在井冈山务农务工。他们朴实善良,知恩图报,孝敬祖先。对于生于斯长于斯的两位侄子,讲他们的苦难家史,讲奶奶在井冈山革命生涯,完全原生态的,充满了井冈山泥土气息,我曾听过,感动不已。我有时不禁沉思,在这个姓氏繁杂的大家族中,我是不是最幸运的一个?是的,但是个例外。
1945年父母亲奉命南下开辟新游击区,也把我向残疾红军、贵州农民杨叔叔托孤,要不是日本在那节骨眼儿投降,我的命运也未可知!所以,虽为一母所生,不若命运的偶然。
我与两个哥哥血脉相通,感情至深,我们唯有感激母亲让我们此生成为兄妹一场。

-
【名家诵名作·朱自清 汤聪】春
2024-03-04 12:39:17 -
【名家说岭南·宋晓琪 汤聪 侯玉婷】把自己活成一道风景
2024-03-03 17:00:12 -
【名家说岭南·汤聪】女人的魅力
2024-03-03 17:00:12 -
【名家说岭南·陶斯亮 侯玉婷】我的大哥几个姓(上篇)
2024-03-02 18:19:3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