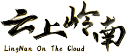
我小时候住的巷子,人口混杂。家门口二十多米外,就是我读书的小学。家后方二十米外,则是一家木雕店。下午一放学,我就跟同巷子的小孩玩丢沙包、跳橡皮筋、拍安仔,要不就去木雕店,看师傅雕木头。
木雕店位于小巷的一个角落,三间房呈品字形。其中一间供师傅一家起居,一间当仓库,放木头,另一间放木雕成品,也是最大的一间。雕木头用的是樟木,要提前两年慢慢阴干,雕出的成品才不会变形。
我常常被那香气吸引,在外面踮起脚尖悄悄往里看。但仓库的窗口很高,我怎么也够不到窗边,只能闻着那股若有若无的香气,像听一段有头没尾的传说。
但放木雕成品的那间房对着路口的墙是落地玻璃做的,木雕就靠着玻璃墙放着。隔着玻璃向里看,那些密密匝匝的木雕,就像在演一场大戏。
有精雕细刻的神龛像,有栩栩如生的演义人物,有活色生香的神像,也有玲珑剔透的摆件。那些人物的眉眼、细小的动作,纤毫毕现,仿佛是真人的缩小版,似乎只要一放大,就可以伴随锣鼓声,铿锵上演一台与大戏台上无二的潮剧。
师傅喜欢把饭桌大小的“五子登科”“麒麟送子”等喜庆木雕正面向外摆放,午后的阳光斜斜地透过玻璃门照在木雕上,映出许多细小的光斑。那是木雕上贴着的金箔在闪光。

有时遇到准备开工的师傅,搬出几段木头,对着光仔细看,就像察看宝石成色的珠宝商,有时凑上前嗅嗅,又像品着酒香的酿酒人。
挑好一段木头,他便带着满意的神情,轻轻将其放在简陋的工作台上——那动作小心翼翼的,像个奶爸放下他初生的孩子。我们则站在一边,满脸虔诚地看着。
师傅四十多岁,黝黑沉默如一段黑色树根。他拿起锤子、凿子,对着铺上图纸的木头敲敲打打,样子比朗诵诗歌还吸引人。
敲打声在巷子里抑扬顿挫地响起,不紧不慢的——不能太紧,怕失手;不能太慢,雕成一件作品要凿很多下,只有维持松弛有度的状态,才能不断干下去。
他绷成一张弓,牙关咬紧,腮边不时鼓起小疙瘩。每凿一下,他就松弛一下,整个人像弹簧,一伸一缩的。不久,他的后颈、手臂会慢慢变得锃亮,上过漆一样,蹦出一颗颗汗珠。粗布的衣服湿成了深色,贴在身上。
被他凿出来的木疙瘩,像碎麻花,慢慢在他脚边堆成高高低低的小丘。樟木香味弥漫在暮色中,直到与家家户户飘出的饭香融合无间,我们才回过神来,此时天已经漆黑,附近都亮起了灯。
接连看了几个黄昏,木雕就慢慢从平面变成立体的——就像连环画里的人物站起来一样。
再过些日子,他用砂纸打磨着那些渐渐流畅的线条,用朱红的颜料涂满了每一个凹凸处,又给木雕贴上金箔,让它如同刚出炉的金首饰一般锃亮。此时再看,你断不会想到,它之前只是一段暗淡的木头。
师傅总在不停地干活。他的生存跟生趣似乎都在锋利的凿子跟刻刀里,镌刻在木头中了。那些成形的木雕放上一些日子,就会消失。
有一天,他忽然跟我们说,那些木雕,大部分会被供在祠堂里。说这话的时候,他眼睛里好像装着刚升起的朝阳。而我们都松了一口气,如得知一个很关心的朋友考上了好学校。
很多年后,我看见一件木雕精品:龙虾蟹篓。几只龙虾跟螃蟹围绕着一个圆形的篓,张牙舞爪,神采飞扬。海边人喜闻乐见的海鲜,被雕出了海龙王的高贵精致。我不由得又想起巷子的暮色里,那个一直埋头敲打着的身影。
他是潮州意溪人,潮州木雕手艺是家传的。
征稿:
《乡音》栏目欢迎投稿。稿件要求具有纪实性,以散文随笔为主,紧扣岭南文化。
投稿请发至邮箱:hdjs@ycwb.com,以“乡音”征文为邮件主题,并请提供详细个人信息。

文/黄春馥
-
【乡音·牛涛 侯玉婷】初秋
2023-08-27 18:30:23 -
【乡音·牛涛 侯玉婷】不再问究竟
2023-08-27 10:01:33 -
优质"致富果" 河源和平猕猴桃种植基地迎来甜蜜丰收
2023-08-25 09:03:27 -
【乡音·牛涛 侯玉婷】寄不出的信
2023-08-24 17:40: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