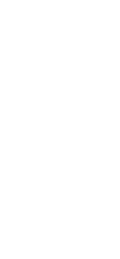文/羊城晚报全媒体记者 黄松炜 杨苑莹
图/羊城晚报全媒体记者 王泽宝 杨苑莹
视频/王泽宝 杨苑莹 黄松炜 罗阳
说起“潮”,你会想起什么?或许会联想到“潮到风湿”的广州东山口,又或者想起上海、成都街头俊男美女。还有一种“潮”,用颜色对话,用涂鸦书写自己的感情。
在顺德IF1959文创园的中庭广场,有一面十余平方米的涂鸦墙。墙上画作出自11位涂鸦人之手,阿奔是其中之一。“我不期待作品保留很久,对我来说,作品完成之后就与我无关了。”也许不是这样。7月5日傍晚,有青年前来打卡,正和该墙合影,在旁的阿奔露出他少见的腼腆笑容。

寻一块涂画之地
涂鸦在英语中以复数Graffiti表示,其单数词为graffito,两词均起源于希腊文,意指“书写”。谈论涂鸦时,通常是指涂鸦人在墙壁上将自己的涂鸦名以签名(tag)、快速涂鸦/泡泡字(throw ups)和高完整性的涂鸦作品(piece)三种不同艺术形式呈现。

“涂鸦人一直在书写自己的名字。以前涂鸦被当作街头的牛皮癣,或者‘小狗撒尿’,到处留印记。”近年来,阿奔看到涂鸦在其他潮流元素的影响下,成为一种国际范儿的“当代艺术、街头艺术、潮流艺术”,人们常在街头、在转角与之相遇。
阿奔是顺德北滘人。小时候,他曾在某些MV里,比如周杰伦的,见过涂鸦墙。涂鸦很酷,和纸上作画完全不同,他买了两瓶喷漆,便动起手来。另一位顺德人杰坤,是“小红书”上的涂鸦红人。他尝试涂鸦,则是为了纪念自己喜欢的明星。
杰坤画过科比,在一个球馆里。那时科比去世不久,他主动联系了一些篮球馆。“我跟他们说,我想纪念科比,请允许我在那里创作。”后来,为了寻找更多供自己创作的“画墙”,杰坤在寻找废弃楼房、厂房之余,常主动联系艺术园区,争取得到他们的许可。

“感谢这个年代”,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进入园区,越来越多的园区接受涂鸦,兔先生说。同样,阿奔需要为自己找到涂画之地。他喜欢自由、安静地创作,不希望被打扰,甚至打断。
据传,每个涂鸦人都有自己的签名和风格。杰坤的tag是“兔先生”,他偏爱写实人物题材,用色大胆,通过营造一种“colorful”的氛围使人感到愉悦。为此,他工作时得用小推车来安放那近百瓶各种颜色的油性漆。他认为,涂鸦是一种表达自我的形式,并不限于在墙上用手喷漆完成。作品只要有涂鸦的“气质”,就可以称之为涂鸦。

另一方面,涂鸦人需熟练用漆,因为涂鸦不像用笔作画,可以慢慢耦合。漆喷出时是雾化状态,得拿捏好雾的特性。“使用喷漆的涂鸦人要快速作画,快速完成每一根线条,这依赖于肌肉记忆,就像滑板一样,通过不断练习来做好动作。”阿奔说。
在阿奔那里,个性、即兴是涂鸦的关键词。他常即兴发挥,“比如路上看到一个被丢弃的娃娃,它就可以出现在我的作品里”。
写在基因里的表达欲望
在IF1959文创园中的篮球滑板主题公园,球场篮球架、滑板U形池均有涂鸦覆盖其上。阿奔和他的团队试图还原90年代美国街区的场景,让年轻人在这里自由表达自己,书写自己的名字。
阿奔的签名是一双“眼睛”,由一个打横的“B”衍化而来。这双眼睛出现在他的所有作品里,“就像在偷偷瞄什么一样”。涂鸦不应该画非原创的东西,那些只是为了吸引流量的,可以称之为墙绘、广告画,总之不是涂鸦。
他还说,涂鸦人就像古代文人,到访某山、某楼,爱题个字、题首诗,留下自己的印记。要是再往前追溯,涂鸦甚至可以说是人类的一种“本质行为”。“远古的人在山洞里凿啊画啊,其实就是涂鸦。小孩子在家里是不是会在墙上乱涂乱写?这是写在我们基因里的表达欲望。”

见面必须画点东西
在顺德IF1959文创园中庭广场的那面涂鸦墙,是该园举办第二届街头艺术节时,由11位涂鸦人共同创作的。阿奔介绍,其中每位都有自己的风格:写中文的,写英文的;可爱的、潮流的……“一个男孩喜欢画兔子,他家里养了兔子。这是他的自画像,抱着一只兔子”。
他记得那天大家到场后即兴交流,“你画什么,我画什么,你画这个,那我可以加点那个。”墙面上,一只巨蛙居高临下,一览众“鸦”小。原来,画青蛙的那位姗姗来迟,大家已画完墙的下半部分,他问:我能画只青蛙压着下面吗?“非常有趣的互动。”阿奔说,共同创作时,大家都想玩得开心一点,不像平时自己创作时那么讲究,更多的是享受过程本身。这也是办街头艺术节的初衷。
他发现,在他们完成那面墙之后,跳舞的人来了,拍穿搭的、打卡的小姐姐、小哥哥们来了。“本来一面大白墙,一面无人问津的墙,没有内容、没有精神,在有了涂鸦之后,更多人关注墙体,来到这里慢慢形成一个‘社群’”。
其实,涂鸦不一定要“上墙”。阿奔会画一些涂鸦风格的手稿,或在帽子、鞋子、滑板、文具等物件上创作。他有一队友,家中几乎所有物品都有涂鸦痕迹。“这是涂鸦人的惯性,也是一种毛病,看到某物就忍不住想要做个标记”。
“‘涂友’,粤语称为‘喷友’。大家以漆会友,见面必须画点东西,否则就不见了。”阿奔说。更为有趣的是,在某处看到有涂鸦画作,大家会心痒痒,想要和他互动一番,“在旁加上几笔”。

不过,涂鸦人之间有一种默契——不随意覆盖他人的作品,否则是对原作者的不尊重。想要互动,就往旁边靠靠。只有当原作品已经褪色严重时,才可考虑进行覆盖。
阿奔和他的Go Back Street团队中的其他人,除了线下共创,也在线上互动。谁去哪里,画了什么,就发到群上,互相交流,彼此鼓励多多创作。他希望通过涂鸦,将所有街头爱好者聚在一处,跳街舞的、玩滑板的,彼此交流、碰撞,也许就能产生更多可能性。
用颜料替代语言
曾有一个主题为关爱自闭症群体的展览,阿奔等6位艺术人用各自的“语言”来表达共同的关怀。例如,有人用自己设计的涂鸦字体,写了一首与自闭症有关的诗,阿奔则创造了一个手拿着星星的卡通形象。
创作者除了他们之外,还有自闭症患者们。作品后来摆在一处,还有一面涂鸦墙供观众书写、表达。“自闭症患者并不擅长用语言表达自己。但在这个空间里,我们不需要语言,我们用颜料替代语言,用颜料去对话”。
阿奔说,无论是涂鸦还是其他美术形式,都是能打破语言“垄断”的交流方式。作品直接影响着人的情绪。“这也是玩涂鸦令我最快乐的地方。”当游客看到自己的某幅作品,开心地与之“合照”时,就是这种影响最直观的证明。
在阿奔看来,街头艺术没有什么门槛。涂鸦画在街头巷尾,就像敞开的“美术馆”,无论来往的人是谁,他们都能瞧见。阿奔在街头创作时,下班从旁走过的工人们也会驻足欣赏,就像“大众画廊一样”。
从这个角度看,阿奔感到涂鸦是开放的,非常有魅力。“不像办展览,每天有多少人买票过来都能清楚。作为创作者,你真的不了解作品会遭遇什么,有怎样的可能性。有人来这里拍视频或者其他?不知道。”

寻找自己涂鸦的可能性
在阿奔看来,涂鸦有太多的可能性。他个人常画鸟类,尤其是凤凰。有一次,他到河北参加全国性的涂鸦交流活动,思考什么才能够代表自己的城市,于是想到了“凤城”——顺德大良街道。
涂鸦成为自己的职业,对于阿奔来说是一桩意外。他还是一名纯爱好者时,时不时有朋友因新开店之类原因,找他去画;他在“小红书”上开了账号,很多机会找他。“是‘商机’找到了我,不是我主动去寻找。”
既然享受涂鸦,那就以此为生。现在,他的日常收入主要来自做“商业涂鸦”或平面设计,他还尝试将涂鸦进行多种跨界联动,比如在醒狮头上涂鸦。在爱好成为职业之后,阿奔努力保持着一种平衡。在工作忙完暂告一段落之后,他就给自己一段空档期,专心创作。
“作品画完之后,与作者已无关,就看墙的生命。”阿奔说,把已完成的作品看得太重,它就成为了负担和压力来源。所以,不要考虑太多的得到或失去,去做就对了。“我不会沉浸在过去的作品里。你问我最满意的作品是哪一幅,我会回答你,下一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