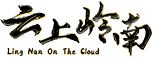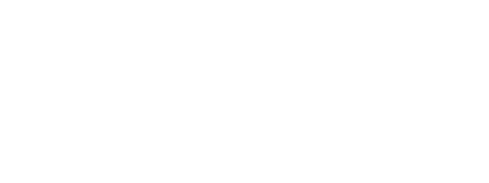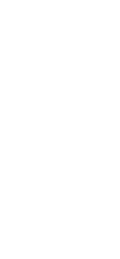上一篇写了七种味道表达的潮汕方言词语。有读者询问,关于味道的概括之词语是什么呢?我想了一想,好像也可以写写。
表示味道的概念,潮汕话跟普通话一样用“味”,但仍然有细微的差别。
潮语的 “味”有两个意思:一、指味觉上的味道,如“臭臊(co1)味”、“海哗(hua3)味”、“芳(pang1)味”、“山气(kui3)味”、“入味”(指煮菜时煮出味道来了)、“辟味”(用特殊作料姜葱等把不好的味道去掉)等,俗语有“白䭕(zian2)无味”(寡淡无味)、 “少食多知味”(平时少吃的东西,赏新时就容易感知其味道之美)。二、指嗅觉上闻到的气味。如“氨水味”、“臭脚液(sioh8)味”、“臭胳囊下味” 等。
但是,味觉和嗅觉感知的味道有时很难分清。我太太曾经请教精细潮菜大师林自然先生关于蒸鱼的时间问题,他指教说,一条鱼蒸多少时间是菜谱里写的,好的厨师都是靠嗅觉感知的,因为鱼的种类、大小、蒸鱼的器皿、火候的大小等随时都有可能不同,一开始水烧开的时候,随蒸汽出来的是一股“臭臊(co1)味”,然后慢慢变成鲜甜。一闻到鲜甜的问道,就是鱼熟了,赶快停火。可见“臭臊味”和“鲜甜味”是既可以由味觉感知,也可以由嗅觉感知的。
咳嗽后的嗓子受损: “个人so5 so5,支声lo5 lo5, 好听过鸭母沕(bhi7, 味)田螺。” 大家伙将就听。
很特殊的是,潮汕话的“味”,前面总要加个特殊的量词,成为“量名结构”,而这些个量词却是与普通话很不相同的。例如:“个味过好/孬” 、“块味过好/孬” ,潮汕话基本不说“一股(gou2)味”。味道明明是味觉感受,为什么潮语会用表示固体形状的“个”(gai5)和“块”(go3)来做量词,我也没搞清楚。我怀疑 gai5和go3的本字可能就是“股”字(古音“见母鱼韵上声”),潮音读go2/go3是没有问题的。
还有说“点味”的,如说:“落加几跳(diaoh4)虾落去吊伊点味起来”(搁几条虾下去把味道提起来)。“点味”大概是强调汤或者菜肴就差那么一点点食材或者作料就可以做出好味道来。
另外,顺便说一下,普通话的“味”指味道有的带儿化,有的没带儿化,意思不一样。因为没有北京人的自然语感,想说好普通话要仔细、认真学习才行,我至今仍然傻傻分不清,没能掌握好。
从“味”又联想起了另一个词——味素,“素” 潮音 sou3(苏3),基本上可以说是“味”的同义词,上面的例子可以替换成为:“个味素过好/孬” 、“块味素过好/孬”。成语有“无味无素”,也是“白䭕无味”的意思。
“味素” 在日语里是味精的意思,也叫“味之素”(味の素)。《现代汉语词典》不收“味素”一词,但却在“味精”条中说:“……也叫味素。” 《汉语大词典》亦然:“味精……也叫味素、味之素。” 搞不清潮语的 “味素” 与日语的“味之素”(味の素)之间有什么关系。
“味素”一词又使我联想起了小时候农村里还有一种叫“尿素”的农田肥料(好像属于氮肥一类)。肥料的作用我不懂,但知道有人用 “尿素袋” 染成蓝色或者黑色后做了裤子穿,昵称 “尿素裤”。尿素袋是用尼龙布做的,那时候绝对是好布料,“尿素” 应该也是从日本进口的吧?但“尿素”的“素”潮音读su3(输3),不读sou3(苏3)。说到题外话了,赶快折回来。
“味道”是靠味蕾、味觉来感知的,气味是靠鼻子、嗅觉来感知的。但潮汕话通常不会用到舌、舌头、味觉、味蕾和闻、嗅这些普通话词语,都以为是 “嘴” 和 “鼻” 的事情,失去味觉和食欲是“嘴涩”,恢复了食欲就是“嘴滑”, 有点像汉语都把思考、思想这些脑力活动当成“心”的活动一样。其他与味道和食欲有关的词语还如:
畏嘴,如说:“新冠阳后嘴涩涩,肥腻个物件食着过畏嘴(新冠)。”
鲜嘴,鲜口,指食物鲜甜美味,如:“只几(gui2)条䖳鱼来煮酸咸菜,鲜嘴死(这几天龙头鱼煮酸菜汤,一定很鲜美。)” 抢嘴,跟“鲜嘴”近义,是指食物鲜美可口。
缀嘴,指吃惯了好东西就老是记住美好的味觉,差一些的就不吃了。如说:“好茶食缀嘴了就孬物,沤(ao3)茶食唔落嘴(好茶喝习惯了,差一些的茶就喝不了了)。”
但要注意的是,“抢嘴抢舌”指的不是抢东西吃,而指抢着说话;“缀嘴缀舌”不是指习惯吃好东西,而是指喜欢学着别人说话,像鹦鹉一样。
乞食身,阿官嘴(身虽穷贱,但对吃还是穷讲究,多用来讽刺身家一般的人对吃的穷讲究)。在著名散文大师秦牧先生的《敝乡茶事甲天下》中,就描写了一位家道败落、沦为乞丐的 “破家阿舍” 做 “乞食” 还带着一把紫砂茶壶跟富人家讨茶喝的“乞食身,阿官嘴”的典型故事。
用来感知味道和气味的“鼻”,是名词用如动词,如“鼻着臭臭(闻起来臭臭的)”、“鼻着芳芳(闻起来香香的)” 等,成语有“听芳鼻臭”(引申指道听途说)。
潮汕话的“鼻”当然也用作名词,指鼻子,如说:“伊支鼻锥锥,四正雅(他的鼻子笔挺,五官端正)。” 新冠病毒上身时的“水泥鼻”,就是“鼻塞” 如有水泥填堵。但引申指鼻涕就有点离谱了,如“流(lao5)鼻”或“鼻流流(lao5)”、“鼻流涎(nuan6)滴”、“爽(sang3)鼻(擤鼻)”,“哼(hngh4)鼻(清鼻涕)”,俗语有“鼻流唔知爽(sang3)”等。比较稀、清的鼻涕,是 “鼻水”,如说 “流鼻水”、“鼻水流流” 等。
“鼻”经常与“嘴”和在一起构词,很特别,成语有“眉目嘴鼻”,泛指五官,五官端正形容为“眉目嘴鼻生来过四正”;“鼻灵嘴精”,意思是精神伶俐;满脸都是灿烂的笑容描写为“嘴笑鼻笑”。但“嘴鼻㩼( zoi7) ” 就不好了,指的是人喜欢说话,不该说的话也说。有时候会造成“着嘴开着嘴累”(因言得祸)。其实,“鼻”是连带着被冤枉的,说话跟鼻子半毛钱关系都没有哦。这在语言学上叫做“偏义复词”,是一种特殊的构词方式。而上文中“听芳鼻臭”的“听”本来指听觉,但在这个成语中指味觉,则属于感觉的转移(词义转移)。普通话的“闻”字“从耳门声”(“听”字繁体“聴”也是从“耳”),本来也是指听觉的,如“闻风而动”、“闻过则改”等,但“闻香识女人”的“闻香”就与潮语的“听芳”异曲同工了,真是有趣。
嘴笑鼻笑:鼻子通了,喉咙通了,深港海关也通了!